历史悠久 始建于 1899 年(光绪25年),至今126年历史。 实力雄厚 医院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医院竞争力?医院排名 100 强榜单”,并在“中...
2025-08-13 65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三甲吗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鹤洞分院
根据《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直属事业单位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025年第一次公开招聘》的规定和报名情况,部分岗位报名人数未达到开考比例。为确保招聘工作正常开展,现延长部分岗位报名时间,并公布考试确认和笔试有关事项,具体公告如下:

一、取消下列岗位招聘
二、延长下列岗位报名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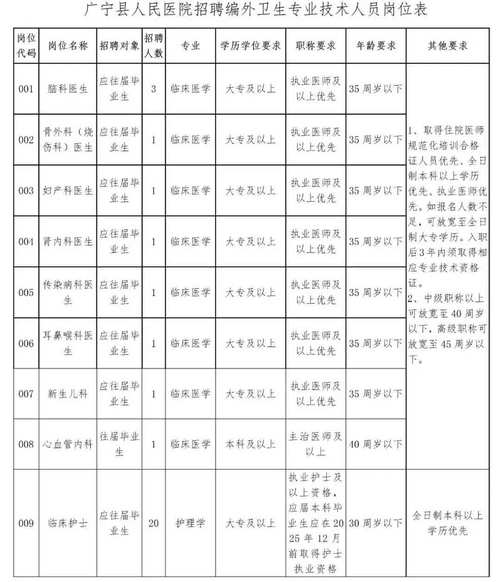
报名时间延至2025年6月27日17:00时,报考资格条件不变。报考条件、报考方式及延长报名岗位的具体要求与原公告一致,原公告链接:http://wjw.gz.gov.cn/xxgk/rsxx/content/post_10300295.html
报名时间延长后,如仍达不到规定的开考比例要求,则按实际符合报名资格条件人数开考。
延长报名资格初审:应聘人员认真填写报名信息,报名系统依据应聘人员所填信息对应聘人员资格条件进行初审,系统初审成功后参加笔试。应聘人员需对系统内填写信息的准确性、真实性负责,资格初审结果在报名系统直接反馈,不另行通知。
三、考试确认
本次公开招聘所有岗位(含第一次公告及本次补充公告延长报名的岗位)通过资格初审的应聘人员(含免笔试考生)于2025年6月29日9:00至2025年6月30日17:00登录报名系统进行考试确认,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考试确认的,视为放弃考试资格,不得参加本次招聘的笔试以及后续的各项环节。
四、准考证打印
通过资格初审和完成报名确认的报考人员请于2025年7月3日9:00起登录报名系统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考证为参加本次公开招聘各个环节的重要证件,请报考人员妥善保管。
报考人员在参加资格审查、面试、体检等环节时,必须同时携带准考证和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与报名时一致),证件不齐的,不得参加考试。不按规定时间、地点参加考试的,视为放弃考试资格。
笔试时间计划安排在2025年7月5日,具体时间及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特此公告。
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5年6月25日
标签: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地址在哪里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鹤洞分院
相关文章

历史悠久 始建于 1899 年(光绪25年),至今126年历史。 实力雄厚 医院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医院竞争力?医院排名 100 强榜单”,并在“中...
2025-08-13 65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三甲吗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鹤洞分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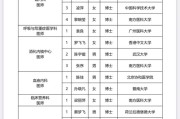
为贯彻广东省“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部署,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人才强市的工作要求,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相关规定,按照“公开、平等、竞争...
2025-08-13 64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和广东省人民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全国排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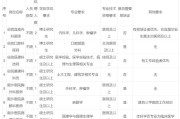
历史悠久 始建于 1899 年(光绪25年),至今126年历史。˂div style="color:#999;text-align:ce...
2025-08-08 111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是三甲吗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领导班子

历史悠久 始建于 1899 年(光绪25年),至今126年历史。 实力雄厚 医院连续多年入选“中国医院竞争力?医院排名 100 强榜单”,并在“中国医...
2025-08-08 65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肾内科主任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鹤洞分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全国排名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