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现代性:私家车如何影响车主的日常生活
拥有私家车,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还是更麻烦?轿车作为一个典型,折射出中国崭新的物质条件和基础设施建设。历时数十年的改革催生出多种多样的出行方式,其中一种是以轿车为中心。在耶鲁大学人类学博士张珺看来,汽车(automobile)更类似于一种“机动车体制(automotive regime)”,既是社会与技术二者聚合的产物,囊括了“人类、机械、空间(包括道路及其他)、代理人、监管机构,还有大量的相关行业及基础设施要素”。张珺指出,美国人和欧洲人已经对机动车体制非常熟悉,因为二战之后,轿车已经成了他们家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把轿车比作宏伟的哥特式大教堂,强调了轿车在当代社会中作为符号的重要象征意义:“所有人都把轿车和教堂二者视为具有魔力的物体,就算不是实用消费品,也是被当做一种形象被消费。”约翰·厄里(John Urry)则考虑到个人的轿车使用体验,提出使用轿车是“步入成年的象征,是公民身份的标志,是社交和人脉的基础”。相比之下,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禁止个人拥有私家车,轿车直到21世纪初才广泛普及。但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10年内,中国便以惊人的速度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轿车市场。随着轿车导向型社会的到来,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不得不投入数十亿资金来大范围建设道路基础设施和交通网。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城市生活的代名词。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机动车体制促进了社会空间和物理层面的流动(下层阶级从中得到的帮助少于精英和中产阶级),机动车体制重置了城市景观,重新谱写了人们日常生活的节奏。近年来,随着与朋友一起驾车出游在中产阶级的休闲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与之相类似的另一种有组织的驾驶实践也变得越来越常见——那便是迎亲车队,这两种集体形式的驾驶实践也引发了张珺的关注。以下内容节选自《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较原文有删节修改。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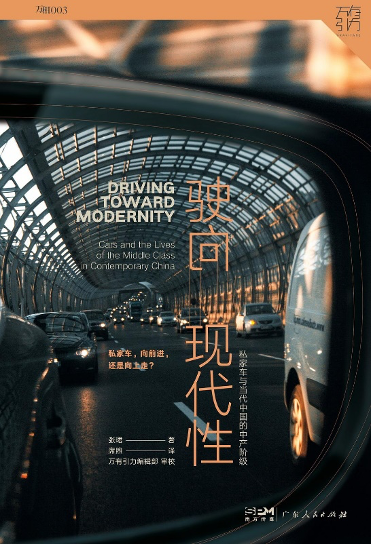 《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张珺 著,席煦 译,万有引力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版。有组织的自驾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随着与朋友一起驾车出游在中产阶级的休闲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些集体形式的驾驶实践——有组织和半组织的自驾游车队或迎亲车队——也变得越来越多。自驾游在中国中产阶级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周末或节假日、国内或国外的旅行中,他们越来越喜欢自驾出游。为个人定制的自驾游越来越多,同时,有组织和半组织的自驾游也在增加。有组织的自驾游通常由企业发起,如汽车制造商、经销商和体育俱乐部,他们组织自驾游来发展业务,并培养客户忠诚度。我为了田野调查而去实习的经销商“汽车之友(Auto-Fan)”就在21世纪初组织了一次自驾游。然而,根据我与该店的经理和几个参加过自驾游的员工的谈话,很难说自驾游在营销方面的效果如何。然而,对参与者来说,集体驾驶的体验比旅途中的风景更生动、更令人印象深刻。那次自驾游后过了几年,“汽车之友”的销售经理卢经理向我讲述时仍然非常兴奋,他还展示了当时的照片:“那次自驾游甚至有警车在前面为我们开路。15辆轿车跟在后面!这不是很棒吗?”袁毅参加了一家汽车制造商通过其经销商组织的自驾游。袁毅在广告行业工作,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袁毅在2003年买了他的第一辆车,是一辆奇瑞QQ。尽管这款车有“廉价”和“不安全”的名声,但它使袁毅跻身同学朋友中最早一批车主的行列。我在2007年见到他的时候,他30岁,那年他刚刚卖掉那辆QQ,买了一辆小巧的紧凑型两厢车,那款轿车是美国品牌,刚上市不久,目标群体是年轻消费者。袁毅喜欢和女朋友,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一起开车旅行。他把他的旅行描述为冒险:“你永远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你。”
《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张珺 著,席煦 译,万有引力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版。有组织的自驾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随着与朋友一起驾车出游在中产阶级的休闲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些集体形式的驾驶实践——有组织和半组织的自驾游车队或迎亲车队——也变得越来越多。自驾游在中国中产阶级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周末或节假日、国内或国外的旅行中,他们越来越喜欢自驾出游。为个人定制的自驾游越来越多,同时,有组织和半组织的自驾游也在增加。有组织的自驾游通常由企业发起,如汽车制造商、经销商和体育俱乐部,他们组织自驾游来发展业务,并培养客户忠诚度。我为了田野调查而去实习的经销商“汽车之友(Auto-Fan)”就在21世纪初组织了一次自驾游。然而,根据我与该店的经理和几个参加过自驾游的员工的谈话,很难说自驾游在营销方面的效果如何。然而,对参与者来说,集体驾驶的体验比旅途中的风景更生动、更令人印象深刻。那次自驾游后过了几年,“汽车之友”的销售经理卢经理向我讲述时仍然非常兴奋,他还展示了当时的照片:“那次自驾游甚至有警车在前面为我们开路。15辆轿车跟在后面!这不是很棒吗?”袁毅参加了一家汽车制造商通过其经销商组织的自驾游。袁毅在广告行业工作,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袁毅在2003年买了他的第一辆车,是一辆奇瑞QQ。尽管这款车有“廉价”和“不安全”的名声,但它使袁毅跻身同学朋友中最早一批车主的行列。我在2007年见到他的时候,他30岁,那年他刚刚卖掉那辆QQ,买了一辆小巧的紧凑型两厢车,那款轿车是美国品牌,刚上市不久,目标群体是年轻消费者。袁毅喜欢和女朋友,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一起开车旅行。他把他的旅行描述为冒险:“你永远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你。” 电视剧《三十而已》(2020)剧照。2007年,袁毅收到经销商的邀请函,被告知他是几十名“幸运”车主之一,被邀请参加一个仅限会员的自驾游活动,目的地是隔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城市。这些“幸运”车主被允许带上朋友和家人一起上路,费用自负。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负责计划路线、住宿、吃饭的地方和其他后勤事宜。组织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所有这些轿车在路上排成一列,为此,他们给每辆车发了一个号码和一个对讲机,车子按照各自的号码排成一列,组织者把经验丰富的司机安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和最后面。通过对讲机,组织者提醒前面的车在有人落后时减速,并告知那些被堵在路上或被红绿灯拦住的司机如何追上车队的其他成员。车队中的所有车辆全程开着应急灯,向其他车辆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是一个团体。有组织的自驾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它把控制和纪律带回到一个本应自由的体验中。袁毅承认,他并不是很喜欢有组织的自驾游,因为“他们限制着你,不让你去你想去的地方”。然而,当他向我讲述他的这次有组织自驾游时,袁毅的眼睛仍闪闪发光。“几十辆车在高速公路上排成一排行驶,所有车的应急灯都在闪,看起来多壮观啊。”由于后勤原因,有组织的自驾游实则给组织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种集体自驾游还有一个更受欢迎的“衍生品”,我称之为“半组织化自驾游”。通常情况下,一群朋友和家人去一个远离家的地方短途旅行。半组织化自驾游没有像上面提到的经销商那样的单一组织者。相反,几个成员一通常是小团体中最热心的人一合作规划行程、路线或项目。他们在城市中靠近高速路入口的某个地方会面,试图组成团体一起开车,闪着应急灯一尤其是在交通繁忙的地区。他们使用对讲机,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比如微信)在开车时与小团体保持联系。在这种自驾游中,彼此的沟通很频繁,不仅是为了让所有的车都在一起,也是为了安排午膳和中途休息的时间,互相开玩笑,评论路上的其他司机和车辆。轿车已取代迎亲车队中的轿子和马的位置半组织化的自驾游与另一种形式的集体驾驶——迎亲车队巡游有许多相似之处。前者在高速公路上或乡村地区更容易见到,而后者在城市里更为寻常和引人关注。迎亲车队通常规模不大,一般由4到6辆车组成。尽管各地情况不同,在传统的婚礼仪式中,往往会有迎亲队伍,里面有抬着新娘的花轿和由苦力抬着的嫁妆,以庆祝两个家庭的结合并展示他们的财富。家庭越富裕、越强大,迎亲队伍规模就越大。如今,轿车已经取代了迎亲车队中的轿子和马的位置。在车队中,主车载着两位新人和首席伴娘伴郎。其余的车则载着其他伴娘、伴郎,有时也载着新人的亲戚,比如表兄弟姐妹、侄女外甥等等。与其他家庭仪式一样,婚礼习俗体现和巩固了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老一辈并不参与迎亲车队巡游。伴娘和伴郎由新人的好友担任,有时则是新人年轻的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迎亲车队中的轿车被称为“花车”,这与“花轿”相呼应,后者是过去婚礼上使用的轿子的名称。新人乘坐的主车引领着巡游队伍,它是车队中最昂贵的一辆,也是装饰得最漂亮的一辆。通常在主车引擎盖顶部靠近汽车品牌标志的地方,会装饰上摆成心形的玫瑰花,或一对毛绒玩具熊,或其他代表新人的可爱卡通形象。其余的“花车”则在车身上装饰有五颜六色的丝带和花朵。它们的装饰非常公式化,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识别它们。轿车行进的顺序是根据它们的昂贵程度来安排的,轿车排在七座面包车之前。越来越多的新人会雇佣一名摄影师来拍摄婚礼的整个过程。摄像师坐的车要么是紧凑型两厢车,要么是带天窗的车,以方便拍摄。大多数时候,摄像师的车在车队最前面行驶,以拍摄整个车队的情况。时不时地,摄影师所坐的车也会绕到车队侧面或后面,从其他角度进行拍摄。两个新人各自的原生家庭之间的地理距离与是否举行婚车巡游无关。即使新郎和新娘的家住得很近,在正式的婚礼上,车队仍然是必需的。在婚礼当天,新郎或他的朋友一大早就把车开到花店,在那里装饰花车。到了吉时,新郎和他的朋友带着车队去接新娘和伴娘,再从新娘的娘家开到新郎的家。回新郎家的路上要绕道而行:车队要穿过有吉祥寓意名字的街道,如吉祥路、多宝路、百子路、泰康路等,以求得好运。
电视剧《三十而已》(2020)剧照。2007年,袁毅收到经销商的邀请函,被告知他是几十名“幸运”车主之一,被邀请参加一个仅限会员的自驾游活动,目的地是隔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城市。这些“幸运”车主被允许带上朋友和家人一起上路,费用自负。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负责计划路线、住宿、吃饭的地方和其他后勤事宜。组织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所有这些轿车在路上排成一列,为此,他们给每辆车发了一个号码和一个对讲机,车子按照各自的号码排成一列,组织者把经验丰富的司机安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和最后面。通过对讲机,组织者提醒前面的车在有人落后时减速,并告知那些被堵在路上或被红绿灯拦住的司机如何追上车队的其他成员。车队中的所有车辆全程开着应急灯,向其他车辆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是一个团体。有组织的自驾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它把控制和纪律带回到一个本应自由的体验中。袁毅承认,他并不是很喜欢有组织的自驾游,因为“他们限制着你,不让你去你想去的地方”。然而,当他向我讲述他的这次有组织自驾游时,袁毅的眼睛仍闪闪发光。“几十辆车在高速公路上排成一排行驶,所有车的应急灯都在闪,看起来多壮观啊。”由于后勤原因,有组织的自驾游实则给组织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种集体自驾游还有一个更受欢迎的“衍生品”,我称之为“半组织化自驾游”。通常情况下,一群朋友和家人去一个远离家的地方短途旅行。半组织化自驾游没有像上面提到的经销商那样的单一组织者。相反,几个成员一通常是小团体中最热心的人一合作规划行程、路线或项目。他们在城市中靠近高速路入口的某个地方会面,试图组成团体一起开车,闪着应急灯一尤其是在交通繁忙的地区。他们使用对讲机,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比如微信)在开车时与小团体保持联系。在这种自驾游中,彼此的沟通很频繁,不仅是为了让所有的车都在一起,也是为了安排午膳和中途休息的时间,互相开玩笑,评论路上的其他司机和车辆。轿车已取代迎亲车队中的轿子和马的位置半组织化的自驾游与另一种形式的集体驾驶——迎亲车队巡游有许多相似之处。前者在高速公路上或乡村地区更容易见到,而后者在城市里更为寻常和引人关注。迎亲车队通常规模不大,一般由4到6辆车组成。尽管各地情况不同,在传统的婚礼仪式中,往往会有迎亲队伍,里面有抬着新娘的花轿和由苦力抬着的嫁妆,以庆祝两个家庭的结合并展示他们的财富。家庭越富裕、越强大,迎亲队伍规模就越大。如今,轿车已经取代了迎亲车队中的轿子和马的位置。在车队中,主车载着两位新人和首席伴娘伴郎。其余的车则载着其他伴娘、伴郎,有时也载着新人的亲戚,比如表兄弟姐妹、侄女外甥等等。与其他家庭仪式一样,婚礼习俗体现和巩固了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老一辈并不参与迎亲车队巡游。伴娘和伴郎由新人的好友担任,有时则是新人年轻的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迎亲车队中的轿车被称为“花车”,这与“花轿”相呼应,后者是过去婚礼上使用的轿子的名称。新人乘坐的主车引领着巡游队伍,它是车队中最昂贵的一辆,也是装饰得最漂亮的一辆。通常在主车引擎盖顶部靠近汽车品牌标志的地方,会装饰上摆成心形的玫瑰花,或一对毛绒玩具熊,或其他代表新人的可爱卡通形象。其余的“花车”则在车身上装饰有五颜六色的丝带和花朵。它们的装饰非常公式化,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识别它们。轿车行进的顺序是根据它们的昂贵程度来安排的,轿车排在七座面包车之前。越来越多的新人会雇佣一名摄影师来拍摄婚礼的整个过程。摄像师坐的车要么是紧凑型两厢车,要么是带天窗的车,以方便拍摄。大多数时候,摄像师的车在车队最前面行驶,以拍摄整个车队的情况。时不时地,摄影师所坐的车也会绕到车队侧面或后面,从其他角度进行拍摄。两个新人各自的原生家庭之间的地理距离与是否举行婚车巡游无关。即使新郎和新娘的家住得很近,在正式的婚礼上,车队仍然是必需的。在婚礼当天,新郎或他的朋友一大早就把车开到花店,在那里装饰花车。到了吉时,新郎和他的朋友带着车队去接新娘和伴娘,再从新娘的娘家开到新郎的家。回新郎家的路上要绕道而行:车队要穿过有吉祥寓意名字的街道,如吉祥路、多宝路、百子路、泰康路等,以求得好运。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2006年至2007年期间,我注意到许多迎亲车队有一个普遍做法,车牌用一张红纸覆盖,红纸上会写上一些诸如“百年好合”和“永结同心”的祝福语。年轻的市场经理斯泰茜开玩笑说,很多人选用的婚车装饰、车牌遮挡和巡航路线都很相似。她曾在2008年收到5张婚礼邀请函,5个婚礼都在同一天。她开玩笑说:“我那天就很担心我坐的花车会跟错车队。”我的访谈对象说这种做法“很常见”。袁毅曾多次担任伴郎和婚车司机。我问他:“你会遮盖车牌吗?这样会违反交通规则吧?”他大笑着向我解释:“不,这些都是花车。结婚是人生大事,交警才不想在这种大日子里为难人。”遮盖车牌的做法持续了一段时间,到21世纪的头10年才逐渐消失。汽车上仍会贴上写着祝福语的红纸,但会贴在车牌的上方或下方。在集体驾驶实践中,保持队形对参与者非常重要婚礼车队首次出现在广州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有车的人相当少,也很少有人持有驾照。大多数人租用出租车和配备司机的面包车来组成迎亲车队。如果新婚夫妇在酒店餐厅举行婚宴,并且总账单超过一定的金额,一些高档酒店就会提供没有“出租车”标志的酒店轿车给新婚夫妇,作为迎亲车队里的主车使用。据一些广州本地居民的回忆称,那时候在婚礼车队里有一辆来自白天鹅宾馆的劳斯莱斯就相当壮观。毕竟当时整个广州也就只有两辆劳斯莱斯。白天鹅宾馆属于一位香港富豪,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广州,这位富豪为此特别购买了两辆劳斯莱斯,当时很多电视和报纸都做了特别报道。因此,在一个大多数人对大多数轿车品牌知之甚少的时代,劳斯莱斯和它的欢乐女神车标在当时被许多当地居民所熟悉。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2006年至2007年期间,我注意到许多迎亲车队有一个普遍做法,车牌用一张红纸覆盖,红纸上会写上一些诸如“百年好合”和“永结同心”的祝福语。年轻的市场经理斯泰茜开玩笑说,很多人选用的婚车装饰、车牌遮挡和巡航路线都很相似。她曾在2008年收到5张婚礼邀请函,5个婚礼都在同一天。她开玩笑说:“我那天就很担心我坐的花车会跟错车队。”我的访谈对象说这种做法“很常见”。袁毅曾多次担任伴郎和婚车司机。我问他:“你会遮盖车牌吗?这样会违反交通规则吧?”他大笑着向我解释:“不,这些都是花车。结婚是人生大事,交警才不想在这种大日子里为难人。”遮盖车牌的做法持续了一段时间,到21世纪的头10年才逐渐消失。汽车上仍会贴上写着祝福语的红纸,但会贴在车牌的上方或下方。在集体驾驶实践中,保持队形对参与者非常重要婚礼车队首次出现在广州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有车的人相当少,也很少有人持有驾照。大多数人租用出租车和配备司机的面包车来组成迎亲车队。如果新婚夫妇在酒店餐厅举行婚宴,并且总账单超过一定的金额,一些高档酒店就会提供没有“出租车”标志的酒店轿车给新婚夫妇,作为迎亲车队里的主车使用。据一些广州本地居民的回忆称,那时候在婚礼车队里有一辆来自白天鹅宾馆的劳斯莱斯就相当壮观。毕竟当时整个广州也就只有两辆劳斯莱斯。白天鹅宾馆属于一位香港富豪,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广州,这位富豪为此特别购买了两辆劳斯莱斯,当时很多电视和报纸都做了特别报道。因此,在一个大多数人对大多数轿车品牌知之甚少的时代,劳斯莱斯和它的欢乐女神车标在当时被许多当地居民所熟悉。 一辆被祝福语遮挡住车牌的婚车,作者摄于2007年。进入新千年,出租车不再出现在广州的迎亲车队伍里。我曾见过只由宝马的7系列或Mini Cooper组成的迎亲车队。面包车则大多被商务车所取代,如别克GL8和本田奥德赛;它们通常供跟车人员乘坐。最经常使用的婚车是中档轿车,如帕萨特、凯美瑞和锐志。通常情况下,这些车既不属于新人也不属于他们的家人。即使他们有一辆车,新婚夫妇仍然要从亲戚、朋友或同事那里借车来组成一个车队。他们尽量借豪华轿车来充当车队的主车。亲近的朋友不仅提供自己的车给新人,还在婚礼当天担任婚车司机。就像有组织的自驾游一样,迎亲车队的所有轿车都排成一列行驶,即使在交通繁忙时也尽量保持在一列。在路上时,婚车会闪应急灯,示意路人他们是一个团体。其他车辆通常不会插进迎亲车队的队列。一些访谈对象告诉我,有时婚车甚至会闯红灯,以便跟上车队的步伐。虽然婚车违反了很多法规条例一遮挡车牌、闯红灯、摄像师不系安全带,但受访者表示交警对婚车的违规行为要比对普通车辆更加容忍。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参加了几场婚礼和一些半组织的自驾游。我注意到,在这些集体驾驶实践中,有一件事对参与者非常重要:保持队形。参与者尽力作为一个团体来驾驶,他们希望街道上的其他车辆能够尊重这一点。如果其他车辆插入他们的车队,他们就会感到不快。我曾在不同场合看到平时很温和、很有礼貌的司机开始咆哮:“他们没看到我的车灯在闪吗?他们没看到这儿有一个车队吗?是个人都看得出!”有时他们会变得很不耐烦,不断地按喇叭,想把别人赶出自己的车道,尽管在城里是禁止按喇叭的。虽然我没有目睹过车队和非车队司机之间的冲突,但有报纸报道,当非车队的司机不尊重车队,不尊重车队保持队形完整的意图时,非车队和车队司机间的冲突就会升级。集体驾驶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从美国的哈雷戴维森车队到日本暴走族(Sato 1991)。这些车手的形象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相联系。这些车队被认为是蔑视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种表达。相比之下,在中国城市中,集体驾驶是非常中产阶级的活动。我的访谈对象中几乎所有车主都参加过迎亲车队巡游和半组织化的自驾游。
一辆被祝福语遮挡住车牌的婚车,作者摄于2007年。进入新千年,出租车不再出现在广州的迎亲车队伍里。我曾见过只由宝马的7系列或Mini Cooper组成的迎亲车队。面包车则大多被商务车所取代,如别克GL8和本田奥德赛;它们通常供跟车人员乘坐。最经常使用的婚车是中档轿车,如帕萨特、凯美瑞和锐志。通常情况下,这些车既不属于新人也不属于他们的家人。即使他们有一辆车,新婚夫妇仍然要从亲戚、朋友或同事那里借车来组成一个车队。他们尽量借豪华轿车来充当车队的主车。亲近的朋友不仅提供自己的车给新人,还在婚礼当天担任婚车司机。就像有组织的自驾游一样,迎亲车队的所有轿车都排成一列行驶,即使在交通繁忙时也尽量保持在一列。在路上时,婚车会闪应急灯,示意路人他们是一个团体。其他车辆通常不会插进迎亲车队的队列。一些访谈对象告诉我,有时婚车甚至会闯红灯,以便跟上车队的步伐。虽然婚车违反了很多法规条例一遮挡车牌、闯红灯、摄像师不系安全带,但受访者表示交警对婚车的违规行为要比对普通车辆更加容忍。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参加了几场婚礼和一些半组织的自驾游。我注意到,在这些集体驾驶实践中,有一件事对参与者非常重要:保持队形。参与者尽力作为一个团体来驾驶,他们希望街道上的其他车辆能够尊重这一点。如果其他车辆插入他们的车队,他们就会感到不快。我曾在不同场合看到平时很温和、很有礼貌的司机开始咆哮:“他们没看到我的车灯在闪吗?他们没看到这儿有一个车队吗?是个人都看得出!”有时他们会变得很不耐烦,不断地按喇叭,想把别人赶出自己的车道,尽管在城里是禁止按喇叭的。虽然我没有目睹过车队和非车队司机之间的冲突,但有报纸报道,当非车队的司机不尊重车队,不尊重车队保持队形完整的意图时,非车队和车队司机间的冲突就会升级。集体驾驶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从美国的哈雷戴维森车队到日本暴走族(Sato 1991)。这些车手的形象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相联系。这些车队被认为是蔑视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种表达。相比之下,在中国城市中,集体驾驶是非常中产阶级的活动。我的访谈对象中几乎所有车主都参加过迎亲车队巡游和半组织化的自驾游。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尽管如此,中国中产阶级的集体驾驶与哈雷戴维森车队仍有共同点:它们都与群体凝聚有关。在这些集体驾驶的场合,中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共同感: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这是一种既独处又共处的体验一各自开着自己的车但同时与同伴相联系。通过一起开车,他们创造了一个共享的社会空间,而这个空间同时又被他们的轿车分隔开。参与者要求他者尊重他们所属的这个社会空间的可见边界;插入车队或中断巡游队伍都是对这个共享空间的践踏。然而,当这些中产阶级司机组成车队,并强调“保持队形”的必要性时,除了群体凝聚和赢得尊重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他们期待着别人尊重车队队形,但除了“我们是一起的”之外,他们说不出为什么这对他们如此重要。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要插入他们的车队?他们担心车队队形被破坏,这种担心与通信无关,因为对讲机、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使他们可以在分开驾驶的同时又能轻易保持联系。这种对队形的迷恋与审美体验有关。我的访谈对象描述这些集体驾驶行为时经常用的说法是“壮观”“看起来很棒”和“感觉很特别这种审美也体现在前文提到的关于“方便”的话语中。轿车能否为其中产阶级车主提高可靠度、带来便利,不仅仅是由汽车品牌决定的;要发挥这种功能,轿车还应该有特定的外观。这种审美体验是历史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它被一系列的国家实践所塑造,并被全球汽车制造商所强化。紧凑型轿车常常被打上某种烙印自从20世纪初汽车出现在中国大城市以来,汽车一直被视为西方现代性和技术的物质体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轿车在高度集体化的环境中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位。虽然国家有意识地发展汽车工业,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轿车往往与剥削成性的城市精英联系在一起。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普通人也可以使用轿车(但通常弄不到车),但中国与上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轿车被看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不适合私人使用。直到1994年,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拥有的乘用车仍占全国总量的大约80%。即使在2006年,中国生产的60万辆乘用车中也只有不到30%卖给了个人。乘用车主要用于党政官员的公务目的。白洁明(Geremier R.Barme)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轿车应用场景:例如,只有党、军队和国家机关的最高级别干部才能乘坐中国制造的新式豪华轿车“红旗”出行。苏联产的“吉姆”是留给部长和省级领导的,“伏尔加”是分配给局长和师级指挥官的,而波兰产的“华沙”是留给普通干部的,他们被戏称为“香烟、油、糖和豆子”干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道路上轿车的主要类型除了非私人用的公务用车之外就是出租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出租车在其他城市已经消失了。由于广交会的召开,国务院在1956年授予广州拥有出租车的权利。出租车队起初为领导人和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服务,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海外华人服务。出租车并不像政府或国有企业的轿车那样享有盛名。然而,乘坐出租车仍然是一种相当昂贵的公共交通方式。对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出生和长大的老广州人来说,“的士”,即英文“出租车(taxi)”一词的粤语音译,泛指任何非政府所有的乘用车。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尽管如此,中国中产阶级的集体驾驶与哈雷戴维森车队仍有共同点:它们都与群体凝聚有关。在这些集体驾驶的场合,中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共同感: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这是一种既独处又共处的体验一各自开着自己的车但同时与同伴相联系。通过一起开车,他们创造了一个共享的社会空间,而这个空间同时又被他们的轿车分隔开。参与者要求他者尊重他们所属的这个社会空间的可见边界;插入车队或中断巡游队伍都是对这个共享空间的践踏。然而,当这些中产阶级司机组成车队,并强调“保持队形”的必要性时,除了群体凝聚和赢得尊重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他们期待着别人尊重车队队形,但除了“我们是一起的”之外,他们说不出为什么这对他们如此重要。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要插入他们的车队?他们担心车队队形被破坏,这种担心与通信无关,因为对讲机、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使他们可以在分开驾驶的同时又能轻易保持联系。这种对队形的迷恋与审美体验有关。我的访谈对象描述这些集体驾驶行为时经常用的说法是“壮观”“看起来很棒”和“感觉很特别这种审美也体现在前文提到的关于“方便”的话语中。轿车能否为其中产阶级车主提高可靠度、带来便利,不仅仅是由汽车品牌决定的;要发挥这种功能,轿车还应该有特定的外观。这种审美体验是历史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它被一系列的国家实践所塑造,并被全球汽车制造商所强化。紧凑型轿车常常被打上某种烙印自从20世纪初汽车出现在中国大城市以来,汽车一直被视为西方现代性和技术的物质体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轿车在高度集体化的环境中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位。虽然国家有意识地发展汽车工业,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轿车往往与剥削成性的城市精英联系在一起。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普通人也可以使用轿车(但通常弄不到车),但中国与上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轿车被看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不适合私人使用。直到1994年,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拥有的乘用车仍占全国总量的大约80%。即使在2006年,中国生产的60万辆乘用车中也只有不到30%卖给了个人。乘用车主要用于党政官员的公务目的。白洁明(Geremier R.Barme)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轿车应用场景:例如,只有党、军队和国家机关的最高级别干部才能乘坐中国制造的新式豪华轿车“红旗”出行。苏联产的“吉姆”是留给部长和省级领导的,“伏尔加”是分配给局长和师级指挥官的,而波兰产的“华沙”是留给普通干部的,他们被戏称为“香烟、油、糖和豆子”干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道路上轿车的主要类型除了非私人用的公务用车之外就是出租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出租车在其他城市已经消失了。由于广交会的召开,国务院在1956年授予广州拥有出租车的权利。出租车队起初为领导人和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服务,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海外华人服务。出租车并不像政府或国有企业的轿车那样享有盛名。然而,乘坐出租车仍然是一种相当昂贵的公共交通方式。对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出生和长大的老广州人来说,“的士”,即英文“出租车(taxi)”一词的粤语音译,泛指任何非政府所有的乘用车。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多年来,公务用车一直保持着相似的外观:它们是中型到大型的黑色轿车,有足够的空间给乘客舒展双腿,还配有一个大后备箱。渴望吸引新兴中产阶级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利用和强化公务车的形象。从2005年到2010年,当大多数主要的国际汽车公司开始在中国生产汽车时,一些公司为中国市场定制了某些车型。一些紧凑型汽车,如标致206,它在欧洲的双门车型在中国被改成了四门车型。其他一些车型,如本田飞度(欧洲的爵士)和标致307,在中国增加了一个后备箱。豪车品牌,如奥迪、宝马和英菲尼迪,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们生产加长轴距的版本,在总长度上增加10到15厘米。例如,奥迪A6被拉长,生产出奥迪A6L。奥迪似乎特别了解中国市场,知道许多人把公务用车的威严外形视为一辆“得体”轿车的标准。我做田野调查的汽车经销店“汽车之友”,有很多客户和我的中年中产阶级访谈对象们一样,都认为深色的中型轿车更“稳重”,更“值得信任”。他们中有人说,这些特征使一辆车看起来“得体”。奥迪似乎已经成功地塑造了其“官车”的形象;许多地方政府将奥迪作为公务用车,而黑色的中档奥迪轿车也赢得了许多如陆律师、秦律师和小王等专业人士的青睐。这种偏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最为明显。在年轻人中,尤其是男性以及律师和国家公务员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偏好。相比之下,紧凑型轿车——根据我许多访谈对象的说法——只适合作为家庭的第二辆车。自2010年以来,紧凑型轿车的数量明显增加,这表明轿车市场也许正在变得多样化。年轻一代的车主,尤其是年轻女性以及一些像袁毅这样的人,认为黑色的四门轿车“无聊”且“缺乏个性”。相反,他们在选择时强调“个性化”。然而,对老年人和中年专业人士来说,“没有屁股(后备箱)的轿车看起来很丑”。紧凑型轿车常常被打上某种烙印:如果车主买的紧凑型车属于低端品牌,就意味着车主买不起更大的轿车。如果小型车是大众甲壳虫或Mini Cooper,它可能被认为是富人的玩具,或是送给情人的礼物,或者是属于一个自我放纵的女人。一些访谈对象解释说,他们的偏好也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他们告诉我,政府喜欢使用某品牌的车是对其质量的一种认可。陆律师对于他为什么选择奥迪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迪要成为政府首选品牌,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它不敢偷工减料。政府官员要求很高;他们的车必须安全且舒适。政府用它家的车,这在中国就是最好的广告和证明。陆律师的说法暗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经常体会到政府、市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中产阶级拥护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让他们获得工作机会和随之而来的丰富商品,但他们对市场力量的道德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政府是遏制市场中任何不道德行为的必要力量。“拥有和驾驶轿车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历史性的经验新兴的中产阶级为当代中国不断走高的轿车销售额提供了动力。然而,中产阶级对轿车的渴望不应该被简单地概括为消费主义所诱发的虚假意识,也不应该把他们对轿车便利性的论述仅仅看作是对虚荣心的修辞性伪装。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和驾驶轿车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历史性的经验。在美国,轿车被认为跨越阶级、性别和种族界限,是自由与自主的终极象征,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颂扬流动性和个人成就的美国主流文化中。然而,正如那培思所认为的,轿车和自由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在中国,买车开车的实践与这些实践所蕴含的意义环环相扣,它们受到各种社会进程的影响和塑造。正是在此过程结构中,是轿车本身,而不是轿车的价格,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轿车是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象征,社会地位向上流动是中产阶级强烈认同的一种价值观。在一个禁止个人拥有轿车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将拥有自己的轿车视作成功的标志。中产阶级通过别人的车来判断别人有多富裕,他们知道自己也处在同样的审视之下。虽然我的访谈对象们声称他们没有参与此类攀比,但他们都认为买车时应当选择“可以被人认出来的”的轿车品牌,且认为这一点很重要。然而,轿车作为社会地位的理想表现形式,并不仅仅是由其经济上的可承受性决定的。一方面,中产阶级承认轿车品牌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但他们对豪华轿车品牌的态度却是模糊的。他们经常拿不同种类的高端轿车和它们的主人开玩笑,并指责新贵们玷污了这些品牌:奔驰和宝马同样都是为富人准备的,但后者往往与傲慢、粗暴、不负责任的新富为伍;而Mini Cooper和甲壳虫则被认为是情人专用。但许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承认,宝马是他们的梦想品牌,奥迪则是高质量轿车的代表。为了区别于那些喜欢通过玛莎拉蒂或跑车等豪车炫耀财富的新贵们,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强调,他们购买或喜欢奥迪等著名品牌,是因为工作需要或这些品牌的造车技术水准。当坐在一起讨论买哪辆车时,这些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通常是男性)经常就各种(众所周知的名牌)轿车型号的工艺、经济、安全性能和美学设计进行激烈——甚至是竞争性的讨论。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多年来,公务用车一直保持着相似的外观:它们是中型到大型的黑色轿车,有足够的空间给乘客舒展双腿,还配有一个大后备箱。渴望吸引新兴中产阶级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利用和强化公务车的形象。从2005年到2010年,当大多数主要的国际汽车公司开始在中国生产汽车时,一些公司为中国市场定制了某些车型。一些紧凑型汽车,如标致206,它在欧洲的双门车型在中国被改成了四门车型。其他一些车型,如本田飞度(欧洲的爵士)和标致307,在中国增加了一个后备箱。豪车品牌,如奥迪、宝马和英菲尼迪,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们生产加长轴距的版本,在总长度上增加10到15厘米。例如,奥迪A6被拉长,生产出奥迪A6L。奥迪似乎特别了解中国市场,知道许多人把公务用车的威严外形视为一辆“得体”轿车的标准。我做田野调查的汽车经销店“汽车之友”,有很多客户和我的中年中产阶级访谈对象们一样,都认为深色的中型轿车更“稳重”,更“值得信任”。他们中有人说,这些特征使一辆车看起来“得体”。奥迪似乎已经成功地塑造了其“官车”的形象;许多地方政府将奥迪作为公务用车,而黑色的中档奥迪轿车也赢得了许多如陆律师、秦律师和小王等专业人士的青睐。这种偏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最为明显。在年轻人中,尤其是男性以及律师和国家公务员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偏好。相比之下,紧凑型轿车——根据我许多访谈对象的说法——只适合作为家庭的第二辆车。自2010年以来,紧凑型轿车的数量明显增加,这表明轿车市场也许正在变得多样化。年轻一代的车主,尤其是年轻女性以及一些像袁毅这样的人,认为黑色的四门轿车“无聊”且“缺乏个性”。相反,他们在选择时强调“个性化”。然而,对老年人和中年专业人士来说,“没有屁股(后备箱)的轿车看起来很丑”。紧凑型轿车常常被打上某种烙印:如果车主买的紧凑型车属于低端品牌,就意味着车主买不起更大的轿车。如果小型车是大众甲壳虫或Mini Cooper,它可能被认为是富人的玩具,或是送给情人的礼物,或者是属于一个自我放纵的女人。一些访谈对象解释说,他们的偏好也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他们告诉我,政府喜欢使用某品牌的车是对其质量的一种认可。陆律师对于他为什么选择奥迪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迪要成为政府首选品牌,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它不敢偷工减料。政府官员要求很高;他们的车必须安全且舒适。政府用它家的车,这在中国就是最好的广告和证明。陆律师的说法暗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经常体会到政府、市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中产阶级拥护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让他们获得工作机会和随之而来的丰富商品,但他们对市场力量的道德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政府是遏制市场中任何不道德行为的必要力量。“拥有和驾驶轿车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历史性的经验新兴的中产阶级为当代中国不断走高的轿车销售额提供了动力。然而,中产阶级对轿车的渴望不应该被简单地概括为消费主义所诱发的虚假意识,也不应该把他们对轿车便利性的论述仅仅看作是对虚荣心的修辞性伪装。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和驾驶轿车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历史性的经验。在美国,轿车被认为跨越阶级、性别和种族界限,是自由与自主的终极象征,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颂扬流动性和个人成就的美国主流文化中。然而,正如那培思所认为的,轿车和自由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在中国,买车开车的实践与这些实践所蕴含的意义环环相扣,它们受到各种社会进程的影响和塑造。正是在此过程结构中,是轿车本身,而不是轿车的价格,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轿车是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象征,社会地位向上流动是中产阶级强烈认同的一种价值观。在一个禁止个人拥有轿车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将拥有自己的轿车视作成功的标志。中产阶级通过别人的车来判断别人有多富裕,他们知道自己也处在同样的审视之下。虽然我的访谈对象们声称他们没有参与此类攀比,但他们都认为买车时应当选择“可以被人认出来的”的轿车品牌,且认为这一点很重要。然而,轿车作为社会地位的理想表现形式,并不仅仅是由其经济上的可承受性决定的。一方面,中产阶级承认轿车品牌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但他们对豪华轿车品牌的态度却是模糊的。他们经常拿不同种类的高端轿车和它们的主人开玩笑,并指责新贵们玷污了这些品牌:奔驰和宝马同样都是为富人准备的,但后者往往与傲慢、粗暴、不负责任的新富为伍;而Mini Cooper和甲壳虫则被认为是情人专用。但许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承认,宝马是他们的梦想品牌,奥迪则是高质量轿车的代表。为了区别于那些喜欢通过玛莎拉蒂或跑车等豪车炫耀财富的新贵们,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强调,他们购买或喜欢奥迪等著名品牌,是因为工作需要或这些品牌的造车技术水准。当坐在一起讨论买哪辆车时,这些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通常是男性)经常就各种(众所周知的名牌)轿车型号的工艺、经济、安全性能和美学设计进行激烈——甚至是竞争性的讨论。 电视剧《三十而已》(2020)剧照。另一方面,轿车的身份效应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复杂关系交织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社会环境下,中产阶级很多在年少时经历过“工作—家庭”空间移动模式,也经历过基础设施匮乏导致的空间流动性低下,对因为社会环境的种种限制而导致的社会流动性低下也有所理解。这些早年的记忆和对缺乏流动性的理解与中产阶层对轿车的渴望息息相关。集体实践也塑造了人们对某些事物和行动的特别感受力;轿车的身份效应也是如此。乘用车曾经仅用于公务。各种形式的轿车巡游到现在仍是表现声势的手段,影响着个人的审美经验。在这样的感知下,中产阶级通过轿车为物质媒介而共同分享某些实践和想象,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和团结性由此建立。那些为了休闲和娱乐而和朋友一起开车的人可能并不打算在朋友面前炫耀他们的成功,但许多坐在车里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同辈压力。在与朋友共进午餐、晚餐或周末出游时,车主可能会问那些没有车的人,他们准备什么时候买车,或者为什么没有买车。像董梅这样的人非常清楚哪些朋友或同事已经买了车,各是什么型号。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焦虑,还有渴望,渴望拥有和朋友及同龄人一样的生活方式。因此,轿车是识别他们同类人的工具,这些人共享一种独特的“工作—家庭”关系、生活节奏和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这种通过轿车获得并由轿车代表的新的流动性不可否认地给中产阶级带来了自由感。这种解放感类似于冰箱和洗衣机带来的解放感:这些技术发明使他们能够兼顾工作、家庭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不同需求和优先次序。轿车连接着空间、时间与人。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以前的生活经历、脑海挥之不去的画面和持续不断的盛大仪式仍对当代实践有着持久的影响。社会性扎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中,当中产阶级享受着轿车带来的控制感和流动性时,他们正在努力重构社会性。原文作者/张珺摘编/何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
电视剧《三十而已》(2020)剧照。另一方面,轿车的身份效应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复杂关系交织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社会环境下,中产阶级很多在年少时经历过“工作—家庭”空间移动模式,也经历过基础设施匮乏导致的空间流动性低下,对因为社会环境的种种限制而导致的社会流动性低下也有所理解。这些早年的记忆和对缺乏流动性的理解与中产阶层对轿车的渴望息息相关。集体实践也塑造了人们对某些事物和行动的特别感受力;轿车的身份效应也是如此。乘用车曾经仅用于公务。各种形式的轿车巡游到现在仍是表现声势的手段,影响着个人的审美经验。在这样的感知下,中产阶级通过轿车为物质媒介而共同分享某些实践和想象,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和团结性由此建立。那些为了休闲和娱乐而和朋友一起开车的人可能并不打算在朋友面前炫耀他们的成功,但许多坐在车里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同辈压力。在与朋友共进午餐、晚餐或周末出游时,车主可能会问那些没有车的人,他们准备什么时候买车,或者为什么没有买车。像董梅这样的人非常清楚哪些朋友或同事已经买了车,各是什么型号。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焦虑,还有渴望,渴望拥有和朋友及同龄人一样的生活方式。因此,轿车是识别他们同类人的工具,这些人共享一种独特的“工作—家庭”关系、生活节奏和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这种通过轿车获得并由轿车代表的新的流动性不可否认地给中产阶级带来了自由感。这种解放感类似于冰箱和洗衣机带来的解放感:这些技术发明使他们能够兼顾工作、家庭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不同需求和优先次序。轿车连接着空间、时间与人。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以前的生活经历、脑海挥之不去的画面和持续不断的盛大仪式仍对当代实践有着持久的影响。社会性扎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中,当中产阶级享受着轿车带来的控制感和流动性时,他们正在努力重构社会性。原文作者/张珺摘编/何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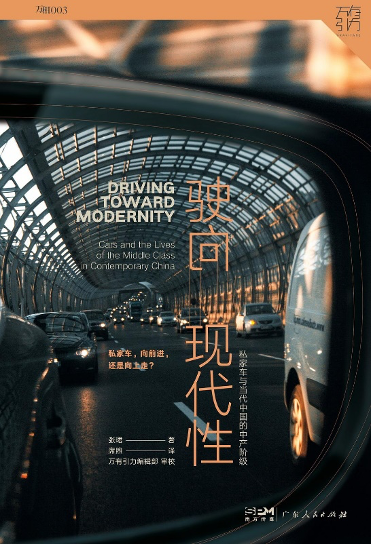 《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张珺 著,席煦 译,万有引力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版。有组织的自驾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随着与朋友一起驾车出游在中产阶级的休闲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些集体形式的驾驶实践——有组织和半组织的自驾游车队或迎亲车队——也变得越来越多。自驾游在中国中产阶级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周末或节假日、国内或国外的旅行中,他们越来越喜欢自驾出游。为个人定制的自驾游越来越多,同时,有组织和半组织的自驾游也在增加。有组织的自驾游通常由企业发起,如汽车制造商、经销商和体育俱乐部,他们组织自驾游来发展业务,并培养客户忠诚度。我为了田野调查而去实习的经销商“汽车之友(Auto-Fan)”就在21世纪初组织了一次自驾游。然而,根据我与该店的经理和几个参加过自驾游的员工的谈话,很难说自驾游在营销方面的效果如何。然而,对参与者来说,集体驾驶的体验比旅途中的风景更生动、更令人印象深刻。那次自驾游后过了几年,“汽车之友”的销售经理卢经理向我讲述时仍然非常兴奋,他还展示了当时的照片:“那次自驾游甚至有警车在前面为我们开路。15辆轿车跟在后面!这不是很棒吗?”袁毅参加了一家汽车制造商通过其经销商组织的自驾游。袁毅在广告行业工作,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袁毅在2003年买了他的第一辆车,是一辆奇瑞QQ。尽管这款车有“廉价”和“不安全”的名声,但它使袁毅跻身同学朋友中最早一批车主的行列。我在2007年见到他的时候,他30岁,那年他刚刚卖掉那辆QQ,买了一辆小巧的紧凑型两厢车,那款轿车是美国品牌,刚上市不久,目标群体是年轻消费者。袁毅喜欢和女朋友,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一起开车旅行。他把他的旅行描述为冒险:“你永远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你。”
《驶向现代性:私家车与当代中国的中产阶级》,张珺 著,席煦 译,万有引力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版。有组织的自驾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随着与朋友一起驾车出游在中产阶级的休闲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一些集体形式的驾驶实践——有组织和半组织的自驾游车队或迎亲车队——也变得越来越多。自驾游在中国中产阶级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在周末或节假日、国内或国外的旅行中,他们越来越喜欢自驾出游。为个人定制的自驾游越来越多,同时,有组织和半组织的自驾游也在增加。有组织的自驾游通常由企业发起,如汽车制造商、经销商和体育俱乐部,他们组织自驾游来发展业务,并培养客户忠诚度。我为了田野调查而去实习的经销商“汽车之友(Auto-Fan)”就在21世纪初组织了一次自驾游。然而,根据我与该店的经理和几个参加过自驾游的员工的谈话,很难说自驾游在营销方面的效果如何。然而,对参与者来说,集体驾驶的体验比旅途中的风景更生动、更令人印象深刻。那次自驾游后过了几年,“汽车之友”的销售经理卢经理向我讲述时仍然非常兴奋,他还展示了当时的照片:“那次自驾游甚至有警车在前面为我们开路。15辆轿车跟在后面!这不是很棒吗?”袁毅参加了一家汽车制造商通过其经销商组织的自驾游。袁毅在广告行业工作,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袁毅在2003年买了他的第一辆车,是一辆奇瑞QQ。尽管这款车有“廉价”和“不安全”的名声,但它使袁毅跻身同学朋友中最早一批车主的行列。我在2007年见到他的时候,他30岁,那年他刚刚卖掉那辆QQ,买了一辆小巧的紧凑型两厢车,那款轿车是美国品牌,刚上市不久,目标群体是年轻消费者。袁毅喜欢和女朋友,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一起开车旅行。他把他的旅行描述为冒险:“你永远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你。” 电视剧《三十而已》(2020)剧照。2007年,袁毅收到经销商的邀请函,被告知他是几十名“幸运”车主之一,被邀请参加一个仅限会员的自驾游活动,目的地是隔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城市。这些“幸运”车主被允许带上朋友和家人一起上路,费用自负。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负责计划路线、住宿、吃饭的地方和其他后勤事宜。组织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所有这些轿车在路上排成一列,为此,他们给每辆车发了一个号码和一个对讲机,车子按照各自的号码排成一列,组织者把经验丰富的司机安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和最后面。通过对讲机,组织者提醒前面的车在有人落后时减速,并告知那些被堵在路上或被红绿灯拦住的司机如何追上车队的其他成员。车队中的所有车辆全程开着应急灯,向其他车辆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是一个团体。有组织的自驾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它把控制和纪律带回到一个本应自由的体验中。袁毅承认,他并不是很喜欢有组织的自驾游,因为“他们限制着你,不让你去你想去的地方”。然而,当他向我讲述他的这次有组织自驾游时,袁毅的眼睛仍闪闪发光。“几十辆车在高速公路上排成一排行驶,所有车的应急灯都在闪,看起来多壮观啊。”由于后勤原因,有组织的自驾游实则给组织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种集体自驾游还有一个更受欢迎的“衍生品”,我称之为“半组织化自驾游”。通常情况下,一群朋友和家人去一个远离家的地方短途旅行。半组织化自驾游没有像上面提到的经销商那样的单一组织者。相反,几个成员一通常是小团体中最热心的人一合作规划行程、路线或项目。他们在城市中靠近高速路入口的某个地方会面,试图组成团体一起开车,闪着应急灯一尤其是在交通繁忙的地区。他们使用对讲机,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比如微信)在开车时与小团体保持联系。在这种自驾游中,彼此的沟通很频繁,不仅是为了让所有的车都在一起,也是为了安排午膳和中途休息的时间,互相开玩笑,评论路上的其他司机和车辆。轿车已取代迎亲车队中的轿子和马的位置半组织化的自驾游与另一种形式的集体驾驶——迎亲车队巡游有许多相似之处。前者在高速公路上或乡村地区更容易见到,而后者在城市里更为寻常和引人关注。迎亲车队通常规模不大,一般由4到6辆车组成。尽管各地情况不同,在传统的婚礼仪式中,往往会有迎亲队伍,里面有抬着新娘的花轿和由苦力抬着的嫁妆,以庆祝两个家庭的结合并展示他们的财富。家庭越富裕、越强大,迎亲队伍规模就越大。如今,轿车已经取代了迎亲车队中的轿子和马的位置。在车队中,主车载着两位新人和首席伴娘伴郎。其余的车则载着其他伴娘、伴郎,有时也载着新人的亲戚,比如表兄弟姐妹、侄女外甥等等。与其他家庭仪式一样,婚礼习俗体现和巩固了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老一辈并不参与迎亲车队巡游。伴娘和伴郎由新人的好友担任,有时则是新人年轻的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迎亲车队中的轿车被称为“花车”,这与“花轿”相呼应,后者是过去婚礼上使用的轿子的名称。新人乘坐的主车引领着巡游队伍,它是车队中最昂贵的一辆,也是装饰得最漂亮的一辆。通常在主车引擎盖顶部靠近汽车品牌标志的地方,会装饰上摆成心形的玫瑰花,或一对毛绒玩具熊,或其他代表新人的可爱卡通形象。其余的“花车”则在车身上装饰有五颜六色的丝带和花朵。它们的装饰非常公式化,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识别它们。轿车行进的顺序是根据它们的昂贵程度来安排的,轿车排在七座面包车之前。越来越多的新人会雇佣一名摄影师来拍摄婚礼的整个过程。摄像师坐的车要么是紧凑型两厢车,要么是带天窗的车,以方便拍摄。大多数时候,摄像师的车在车队最前面行驶,以拍摄整个车队的情况。时不时地,摄影师所坐的车也会绕到车队侧面或后面,从其他角度进行拍摄。两个新人各自的原生家庭之间的地理距离与是否举行婚车巡游无关。即使新郎和新娘的家住得很近,在正式的婚礼上,车队仍然是必需的。在婚礼当天,新郎或他的朋友一大早就把车开到花店,在那里装饰花车。到了吉时,新郎和他的朋友带着车队去接新娘和伴娘,再从新娘的娘家开到新郎的家。回新郎家的路上要绕道而行:车队要穿过有吉祥寓意名字的街道,如吉祥路、多宝路、百子路、泰康路等,以求得好运。
电视剧《三十而已》(2020)剧照。2007年,袁毅收到经销商的邀请函,被告知他是几十名“幸运”车主之一,被邀请参加一个仅限会员的自驾游活动,目的地是隔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一个城市。这些“幸运”车主被允许带上朋友和家人一起上路,费用自负。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负责计划路线、住宿、吃饭的地方和其他后勤事宜。组织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所有这些轿车在路上排成一列,为此,他们给每辆车发了一个号码和一个对讲机,车子按照各自的号码排成一列,组织者把经验丰富的司机安排在队伍的最前面和最后面。通过对讲机,组织者提醒前面的车在有人落后时减速,并告知那些被堵在路上或被红绿灯拦住的司机如何追上车队的其他成员。车队中的所有车辆全程开着应急灯,向其他车辆发出信号,表明他们是一个团体。有组织的自驾游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它把控制和纪律带回到一个本应自由的体验中。袁毅承认,他并不是很喜欢有组织的自驾游,因为“他们限制着你,不让你去你想去的地方”。然而,当他向我讲述他的这次有组织自驾游时,袁毅的眼睛仍闪闪发光。“几十辆车在高速公路上排成一排行驶,所有车的应急灯都在闪,看起来多壮观啊。”由于后勤原因,有组织的自驾游实则给组织者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种集体自驾游还有一个更受欢迎的“衍生品”,我称之为“半组织化自驾游”。通常情况下,一群朋友和家人去一个远离家的地方短途旅行。半组织化自驾游没有像上面提到的经销商那样的单一组织者。相反,几个成员一通常是小团体中最热心的人一合作规划行程、路线或项目。他们在城市中靠近高速路入口的某个地方会面,试图组成团体一起开车,闪着应急灯一尤其是在交通繁忙的地区。他们使用对讲机,也越来越多地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比如微信)在开车时与小团体保持联系。在这种自驾游中,彼此的沟通很频繁,不仅是为了让所有的车都在一起,也是为了安排午膳和中途休息的时间,互相开玩笑,评论路上的其他司机和车辆。轿车已取代迎亲车队中的轿子和马的位置半组织化的自驾游与另一种形式的集体驾驶——迎亲车队巡游有许多相似之处。前者在高速公路上或乡村地区更容易见到,而后者在城市里更为寻常和引人关注。迎亲车队通常规模不大,一般由4到6辆车组成。尽管各地情况不同,在传统的婚礼仪式中,往往会有迎亲队伍,里面有抬着新娘的花轿和由苦力抬着的嫁妆,以庆祝两个家庭的结合并展示他们的财富。家庭越富裕、越强大,迎亲队伍规模就越大。如今,轿车已经取代了迎亲车队中的轿子和马的位置。在车队中,主车载着两位新人和首席伴娘伴郎。其余的车则载着其他伴娘、伴郎,有时也载着新人的亲戚,比如表兄弟姐妹、侄女外甥等等。与其他家庭仪式一样,婚礼习俗体现和巩固了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老一辈并不参与迎亲车队巡游。伴娘和伴郎由新人的好友担任,有时则是新人年轻的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迎亲车队中的轿车被称为“花车”,这与“花轿”相呼应,后者是过去婚礼上使用的轿子的名称。新人乘坐的主车引领着巡游队伍,它是车队中最昂贵的一辆,也是装饰得最漂亮的一辆。通常在主车引擎盖顶部靠近汽车品牌标志的地方,会装饰上摆成心形的玫瑰花,或一对毛绒玩具熊,或其他代表新人的可爱卡通形象。其余的“花车”则在车身上装饰有五颜六色的丝带和花朵。它们的装饰非常公式化,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识别它们。轿车行进的顺序是根据它们的昂贵程度来安排的,轿车排在七座面包车之前。越来越多的新人会雇佣一名摄影师来拍摄婚礼的整个过程。摄像师坐的车要么是紧凑型两厢车,要么是带天窗的车,以方便拍摄。大多数时候,摄像师的车在车队最前面行驶,以拍摄整个车队的情况。时不时地,摄影师所坐的车也会绕到车队侧面或后面,从其他角度进行拍摄。两个新人各自的原生家庭之间的地理距离与是否举行婚车巡游无关。即使新郎和新娘的家住得很近,在正式的婚礼上,车队仍然是必需的。在婚礼当天,新郎或他的朋友一大早就把车开到花店,在那里装饰花车。到了吉时,新郎和他的朋友带着车队去接新娘和伴娘,再从新娘的娘家开到新郎的家。回新郎家的路上要绕道而行:车队要穿过有吉祥寓意名字的街道,如吉祥路、多宝路、百子路、泰康路等,以求得好运。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2006年至2007年期间,我注意到许多迎亲车队有一个普遍做法,车牌用一张红纸覆盖,红纸上会写上一些诸如“百年好合”和“永结同心”的祝福语。年轻的市场经理斯泰茜开玩笑说,很多人选用的婚车装饰、车牌遮挡和巡航路线都很相似。她曾在2008年收到5张婚礼邀请函,5个婚礼都在同一天。她开玩笑说:“我那天就很担心我坐的花车会跟错车队。”我的访谈对象说这种做法“很常见”。袁毅曾多次担任伴郎和婚车司机。我问他:“你会遮盖车牌吗?这样会违反交通规则吧?”他大笑着向我解释:“不,这些都是花车。结婚是人生大事,交警才不想在这种大日子里为难人。”遮盖车牌的做法持续了一段时间,到21世纪的头10年才逐渐消失。汽车上仍会贴上写着祝福语的红纸,但会贴在车牌的上方或下方。在集体驾驶实践中,保持队形对参与者非常重要婚礼车队首次出现在广州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有车的人相当少,也很少有人持有驾照。大多数人租用出租车和配备司机的面包车来组成迎亲车队。如果新婚夫妇在酒店餐厅举行婚宴,并且总账单超过一定的金额,一些高档酒店就会提供没有“出租车”标志的酒店轿车给新婚夫妇,作为迎亲车队里的主车使用。据一些广州本地居民的回忆称,那时候在婚礼车队里有一辆来自白天鹅宾馆的劳斯莱斯就相当壮观。毕竟当时整个广州也就只有两辆劳斯莱斯。白天鹅宾馆属于一位香港富豪,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广州,这位富豪为此特别购买了两辆劳斯莱斯,当时很多电视和报纸都做了特别报道。因此,在一个大多数人对大多数轿车品牌知之甚少的时代,劳斯莱斯和它的欢乐女神车标在当时被许多当地居民所熟悉。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2006年至2007年期间,我注意到许多迎亲车队有一个普遍做法,车牌用一张红纸覆盖,红纸上会写上一些诸如“百年好合”和“永结同心”的祝福语。年轻的市场经理斯泰茜开玩笑说,很多人选用的婚车装饰、车牌遮挡和巡航路线都很相似。她曾在2008年收到5张婚礼邀请函,5个婚礼都在同一天。她开玩笑说:“我那天就很担心我坐的花车会跟错车队。”我的访谈对象说这种做法“很常见”。袁毅曾多次担任伴郎和婚车司机。我问他:“你会遮盖车牌吗?这样会违反交通规则吧?”他大笑着向我解释:“不,这些都是花车。结婚是人生大事,交警才不想在这种大日子里为难人。”遮盖车牌的做法持续了一段时间,到21世纪的头10年才逐渐消失。汽车上仍会贴上写着祝福语的红纸,但会贴在车牌的上方或下方。在集体驾驶实践中,保持队形对参与者非常重要婚礼车队首次出现在广州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有车的人相当少,也很少有人持有驾照。大多数人租用出租车和配备司机的面包车来组成迎亲车队。如果新婚夫妇在酒店餐厅举行婚宴,并且总账单超过一定的金额,一些高档酒店就会提供没有“出租车”标志的酒店轿车给新婚夫妇,作为迎亲车队里的主车使用。据一些广州本地居民的回忆称,那时候在婚礼车队里有一辆来自白天鹅宾馆的劳斯莱斯就相当壮观。毕竟当时整个广州也就只有两辆劳斯莱斯。白天鹅宾馆属于一位香港富豪,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问广州,这位富豪为此特别购买了两辆劳斯莱斯,当时很多电视和报纸都做了特别报道。因此,在一个大多数人对大多数轿车品牌知之甚少的时代,劳斯莱斯和它的欢乐女神车标在当时被许多当地居民所熟悉。 一辆被祝福语遮挡住车牌的婚车,作者摄于2007年。进入新千年,出租车不再出现在广州的迎亲车队伍里。我曾见过只由宝马的7系列或Mini Cooper组成的迎亲车队。面包车则大多被商务车所取代,如别克GL8和本田奥德赛;它们通常供跟车人员乘坐。最经常使用的婚车是中档轿车,如帕萨特、凯美瑞和锐志。通常情况下,这些车既不属于新人也不属于他们的家人。即使他们有一辆车,新婚夫妇仍然要从亲戚、朋友或同事那里借车来组成一个车队。他们尽量借豪华轿车来充当车队的主车。亲近的朋友不仅提供自己的车给新人,还在婚礼当天担任婚车司机。就像有组织的自驾游一样,迎亲车队的所有轿车都排成一列行驶,即使在交通繁忙时也尽量保持在一列。在路上时,婚车会闪应急灯,示意路人他们是一个团体。其他车辆通常不会插进迎亲车队的队列。一些访谈对象告诉我,有时婚车甚至会闯红灯,以便跟上车队的步伐。虽然婚车违反了很多法规条例一遮挡车牌、闯红灯、摄像师不系安全带,但受访者表示交警对婚车的违规行为要比对普通车辆更加容忍。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参加了几场婚礼和一些半组织的自驾游。我注意到,在这些集体驾驶实践中,有一件事对参与者非常重要:保持队形。参与者尽力作为一个团体来驾驶,他们希望街道上的其他车辆能够尊重这一点。如果其他车辆插入他们的车队,他们就会感到不快。我曾在不同场合看到平时很温和、很有礼貌的司机开始咆哮:“他们没看到我的车灯在闪吗?他们没看到这儿有一个车队吗?是个人都看得出!”有时他们会变得很不耐烦,不断地按喇叭,想把别人赶出自己的车道,尽管在城里是禁止按喇叭的。虽然我没有目睹过车队和非车队司机之间的冲突,但有报纸报道,当非车队的司机不尊重车队,不尊重车队保持队形完整的意图时,非车队和车队司机间的冲突就会升级。集体驾驶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从美国的哈雷戴维森车队到日本暴走族(Sato 1991)。这些车手的形象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相联系。这些车队被认为是蔑视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种表达。相比之下,在中国城市中,集体驾驶是非常中产阶级的活动。我的访谈对象中几乎所有车主都参加过迎亲车队巡游和半组织化的自驾游。
一辆被祝福语遮挡住车牌的婚车,作者摄于2007年。进入新千年,出租车不再出现在广州的迎亲车队伍里。我曾见过只由宝马的7系列或Mini Cooper组成的迎亲车队。面包车则大多被商务车所取代,如别克GL8和本田奥德赛;它们通常供跟车人员乘坐。最经常使用的婚车是中档轿车,如帕萨特、凯美瑞和锐志。通常情况下,这些车既不属于新人也不属于他们的家人。即使他们有一辆车,新婚夫妇仍然要从亲戚、朋友或同事那里借车来组成一个车队。他们尽量借豪华轿车来充当车队的主车。亲近的朋友不仅提供自己的车给新人,还在婚礼当天担任婚车司机。就像有组织的自驾游一样,迎亲车队的所有轿车都排成一列行驶,即使在交通繁忙时也尽量保持在一列。在路上时,婚车会闪应急灯,示意路人他们是一个团体。其他车辆通常不会插进迎亲车队的队列。一些访谈对象告诉我,有时婚车甚至会闯红灯,以便跟上车队的步伐。虽然婚车违反了很多法规条例一遮挡车牌、闯红灯、摄像师不系安全带,但受访者表示交警对婚车的违规行为要比对普通车辆更加容忍。在多年的田野调查中,我参加了几场婚礼和一些半组织的自驾游。我注意到,在这些集体驾驶实践中,有一件事对参与者非常重要:保持队形。参与者尽力作为一个团体来驾驶,他们希望街道上的其他车辆能够尊重这一点。如果其他车辆插入他们的车队,他们就会感到不快。我曾在不同场合看到平时很温和、很有礼貌的司机开始咆哮:“他们没看到我的车灯在闪吗?他们没看到这儿有一个车队吗?是个人都看得出!”有时他们会变得很不耐烦,不断地按喇叭,想把别人赶出自己的车道,尽管在城里是禁止按喇叭的。虽然我没有目睹过车队和非车队司机之间的冲突,但有报纸报道,当非车队的司机不尊重车队,不尊重车队保持队形完整的意图时,非车队和车队司机间的冲突就会升级。集体驾驶的做法在其他国家也存在。从美国的哈雷戴维森车队到日本暴走族(Sato 1991)。这些车手的形象与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身份认同相联系。这些车队被认为是蔑视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一种表达。相比之下,在中国城市中,集体驾驶是非常中产阶级的活动。我的访谈对象中几乎所有车主都参加过迎亲车队巡游和半组织化的自驾游。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尽管如此,中国中产阶级的集体驾驶与哈雷戴维森车队仍有共同点:它们都与群体凝聚有关。在这些集体驾驶的场合,中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共同感: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这是一种既独处又共处的体验一各自开着自己的车但同时与同伴相联系。通过一起开车,他们创造了一个共享的社会空间,而这个空间同时又被他们的轿车分隔开。参与者要求他者尊重他们所属的这个社会空间的可见边界;插入车队或中断巡游队伍都是对这个共享空间的践踏。然而,当这些中产阶级司机组成车队,并强调“保持队形”的必要性时,除了群体凝聚和赢得尊重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他们期待着别人尊重车队队形,但除了“我们是一起的”之外,他们说不出为什么这对他们如此重要。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要插入他们的车队?他们担心车队队形被破坏,这种担心与通信无关,因为对讲机、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使他们可以在分开驾驶的同时又能轻易保持联系。这种对队形的迷恋与审美体验有关。我的访谈对象描述这些集体驾驶行为时经常用的说法是“壮观”“看起来很棒”和“感觉很特别这种审美也体现在前文提到的关于“方便”的话语中。轿车能否为其中产阶级车主提高可靠度、带来便利,不仅仅是由汽车品牌决定的;要发挥这种功能,轿车还应该有特定的外观。这种审美体验是历史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它被一系列的国家实践所塑造,并被全球汽车制造商所强化。紧凑型轿车常常被打上某种烙印自从20世纪初汽车出现在中国大城市以来,汽车一直被视为西方现代性和技术的物质体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轿车在高度集体化的环境中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位。虽然国家有意识地发展汽车工业,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轿车往往与剥削成性的城市精英联系在一起。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普通人也可以使用轿车(但通常弄不到车),但中国与上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轿车被看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不适合私人使用。直到1994年,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拥有的乘用车仍占全国总量的大约80%。即使在2006年,中国生产的60万辆乘用车中也只有不到30%卖给了个人。乘用车主要用于党政官员的公务目的。白洁明(Geremier R.Barme)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轿车应用场景:例如,只有党、军队和国家机关的最高级别干部才能乘坐中国制造的新式豪华轿车“红旗”出行。苏联产的“吉姆”是留给部长和省级领导的,“伏尔加”是分配给局长和师级指挥官的,而波兰产的“华沙”是留给普通干部的,他们被戏称为“香烟、油、糖和豆子”干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道路上轿车的主要类型除了非私人用的公务用车之外就是出租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出租车在其他城市已经消失了。由于广交会的召开,国务院在1956年授予广州拥有出租车的权利。出租车队起初为领导人和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服务,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海外华人服务。出租车并不像政府或国有企业的轿车那样享有盛名。然而,乘坐出租车仍然是一种相当昂贵的公共交通方式。对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出生和长大的老广州人来说,“的士”,即英文“出租车(taxi)”一词的粤语音译,泛指任何非政府所有的乘用车。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尽管如此,中国中产阶级的集体驾驶与哈雷戴维森车队仍有共同点:它们都与群体凝聚有关。在这些集体驾驶的场合,中产阶级感受到一种共同感: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这是一种既独处又共处的体验一各自开着自己的车但同时与同伴相联系。通过一起开车,他们创造了一个共享的社会空间,而这个空间同时又被他们的轿车分隔开。参与者要求他者尊重他们所属的这个社会空间的可见边界;插入车队或中断巡游队伍都是对这个共享空间的践踏。然而,当这些中产阶级司机组成车队,并强调“保持队形”的必要性时,除了群体凝聚和赢得尊重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他们期待着别人尊重车队队形,但除了“我们是一起的”之外,他们说不出为什么这对他们如此重要。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其他人要插入他们的车队?他们担心车队队形被破坏,这种担心与通信无关,因为对讲机、移动电话和互联网使他们可以在分开驾驶的同时又能轻易保持联系。这种对队形的迷恋与审美体验有关。我的访谈对象描述这些集体驾驶行为时经常用的说法是“壮观”“看起来很棒”和“感觉很特别这种审美也体现在前文提到的关于“方便”的话语中。轿车能否为其中产阶级车主提高可靠度、带来便利,不仅仅是由汽车品牌决定的;要发挥这种功能,轿车还应该有特定的外观。这种审美体验是历史性的,在很大程度上,它被一系列的国家实践所塑造,并被全球汽车制造商所强化。紧凑型轿车常常被打上某种烙印自从20世纪初汽车出现在中国大城市以来,汽车一直被视为西方现代性和技术的物质体现。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轿车在高度集体化的环境中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位。虽然国家有意识地发展汽车工业,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轿车往往与剥削成性的城市精英联系在一起。在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普通人也可以使用轿车(但通常弄不到车),但中国与上述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同。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中国,轿车被看做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因此不适合私人使用。直到1994年,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拥有的乘用车仍占全国总量的大约80%。即使在2006年,中国生产的60万辆乘用车中也只有不到30%卖给了个人。乘用车主要用于党政官员的公务目的。白洁明(Geremier R.Barme)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中国的轿车应用场景:例如,只有党、军队和国家机关的最高级别干部才能乘坐中国制造的新式豪华轿车“红旗”出行。苏联产的“吉姆”是留给部长和省级领导的,“伏尔加”是分配给局长和师级指挥官的,而波兰产的“华沙”是留给普通干部的,他们被戏称为“香烟、油、糖和豆子”干部。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道路上轿车的主要类型除了非私人用的公务用车之外就是出租车。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出租车在其他城市已经消失了。由于广交会的召开,国务院在1956年授予广州拥有出租车的权利。出租车队起初为领导人和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服务,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为海外华人服务。出租车并不像政府或国有企业的轿车那样享有盛名。然而,乘坐出租车仍然是一种相当昂贵的公共交通方式。对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出生和长大的老广州人来说,“的士”,即英文“出租车(taxi)”一词的粤语音译,泛指任何非政府所有的乘用车。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多年来,公务用车一直保持着相似的外观:它们是中型到大型的黑色轿车,有足够的空间给乘客舒展双腿,还配有一个大后备箱。渴望吸引新兴中产阶级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利用和强化公务车的形象。从2005年到2010年,当大多数主要的国际汽车公司开始在中国生产汽车时,一些公司为中国市场定制了某些车型。一些紧凑型汽车,如标致206,它在欧洲的双门车型在中国被改成了四门车型。其他一些车型,如本田飞度(欧洲的爵士)和标致307,在中国增加了一个后备箱。豪车品牌,如奥迪、宝马和英菲尼迪,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们生产加长轴距的版本,在总长度上增加10到15厘米。例如,奥迪A6被拉长,生产出奥迪A6L。奥迪似乎特别了解中国市场,知道许多人把公务用车的威严外形视为一辆“得体”轿车的标准。我做田野调查的汽车经销店“汽车之友”,有很多客户和我的中年中产阶级访谈对象们一样,都认为深色的中型轿车更“稳重”,更“值得信任”。他们中有人说,这些特征使一辆车看起来“得体”。奥迪似乎已经成功地塑造了其“官车”的形象;许多地方政府将奥迪作为公务用车,而黑色的中档奥迪轿车也赢得了许多如陆律师、秦律师和小王等专业人士的青睐。这种偏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最为明显。在年轻人中,尤其是男性以及律师和国家公务员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偏好。相比之下,紧凑型轿车——根据我许多访谈对象的说法——只适合作为家庭的第二辆车。自2010年以来,紧凑型轿车的数量明显增加,这表明轿车市场也许正在变得多样化。年轻一代的车主,尤其是年轻女性以及一些像袁毅这样的人,认为黑色的四门轿车“无聊”且“缺乏个性”。相反,他们在选择时强调“个性化”。然而,对老年人和中年专业人士来说,“没有屁股(后备箱)的轿车看起来很丑”。紧凑型轿车常常被打上某种烙印:如果车主买的紧凑型车属于低端品牌,就意味着车主买不起更大的轿车。如果小型车是大众甲壳虫或Mini Cooper,它可能被认为是富人的玩具,或是送给情人的礼物,或者是属于一个自我放纵的女人。一些访谈对象解释说,他们的偏好也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他们告诉我,政府喜欢使用某品牌的车是对其质量的一种认可。陆律师对于他为什么选择奥迪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迪要成为政府首选品牌,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它不敢偷工减料。政府官员要求很高;他们的车必须安全且舒适。政府用它家的车,这在中国就是最好的广告和证明。陆律师的说法暗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经常体会到政府、市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中产阶级拥护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让他们获得工作机会和随之而来的丰富商品,但他们对市场力量的道德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政府是遏制市场中任何不道德行为的必要力量。“拥有和驾驶轿车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历史性的经验新兴的中产阶级为当代中国不断走高的轿车销售额提供了动力。然而,中产阶级对轿车的渴望不应该被简单地概括为消费主义所诱发的虚假意识,也不应该把他们对轿车便利性的论述仅仅看作是对虚荣心的修辞性伪装。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和驾驶轿车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历史性的经验。在美国,轿车被认为跨越阶级、性别和种族界限,是自由与自主的终极象征,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颂扬流动性和个人成就的美国主流文化中。然而,正如那培思所认为的,轿车和自由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在中国,买车开车的实践与这些实践所蕴含的意义环环相扣,它们受到各种社会进程的影响和塑造。正是在此过程结构中,是轿车本身,而不是轿车的价格,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轿车是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象征,社会地位向上流动是中产阶级强烈认同的一种价值观。在一个禁止个人拥有轿车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将拥有自己的轿车视作成功的标志。中产阶级通过别人的车来判断别人有多富裕,他们知道自己也处在同样的审视之下。虽然我的访谈对象们声称他们没有参与此类攀比,但他们都认为买车时应当选择“可以被人认出来的”的轿车品牌,且认为这一点很重要。然而,轿车作为社会地位的理想表现形式,并不仅仅是由其经济上的可承受性决定的。一方面,中产阶级承认轿车品牌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但他们对豪华轿车品牌的态度却是模糊的。他们经常拿不同种类的高端轿车和它们的主人开玩笑,并指责新贵们玷污了这些品牌:奔驰和宝马同样都是为富人准备的,但后者往往与傲慢、粗暴、不负责任的新富为伍;而Mini Cooper和甲壳虫则被认为是情人专用。但许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承认,宝马是他们的梦想品牌,奥迪则是高质量轿车的代表。为了区别于那些喜欢通过玛莎拉蒂或跑车等豪车炫耀财富的新贵们,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强调,他们购买或喜欢奥迪等著名品牌,是因为工作需要或这些品牌的造车技术水准。当坐在一起讨论买哪辆车时,这些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通常是男性)经常就各种(众所周知的名牌)轿车型号的工艺、经济、安全性能和美学设计进行激烈——甚至是竞争性的讨论。
电影《人生路不熟》(2023)剧照。多年来,公务用车一直保持着相似的外观:它们是中型到大型的黑色轿车,有足够的空间给乘客舒展双腿,还配有一个大后备箱。渴望吸引新兴中产阶级的国际汽车制造商一直在利用和强化公务车的形象。从2005年到2010年,当大多数主要的国际汽车公司开始在中国生产汽车时,一些公司为中国市场定制了某些车型。一些紧凑型汽车,如标致206,它在欧洲的双门车型在中国被改成了四门车型。其他一些车型,如本田飞度(欧洲的爵士)和标致307,在中国增加了一个后备箱。豪车品牌,如奥迪、宝马和英菲尼迪,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他们生产加长轴距的版本,在总长度上增加10到15厘米。例如,奥迪A6被拉长,生产出奥迪A6L。奥迪似乎特别了解中国市场,知道许多人把公务用车的威严外形视为一辆“得体”轿车的标准。我做田野调查的汽车经销店“汽车之友”,有很多客户和我的中年中产阶级访谈对象们一样,都认为深色的中型轿车更“稳重”,更“值得信任”。他们中有人说,这些特征使一辆车看起来“得体”。奥迪似乎已经成功地塑造了其“官车”的形象;许多地方政府将奥迪作为公务用车,而黑色的中档奥迪轿车也赢得了许多如陆律师、秦律师和小王等专业人士的青睐。这种偏好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最为明显。在年轻人中,尤其是男性以及律师和国家公务员中,也可以看到这种偏好。相比之下,紧凑型轿车——根据我许多访谈对象的说法——只适合作为家庭的第二辆车。自2010年以来,紧凑型轿车的数量明显增加,这表明轿车市场也许正在变得多样化。年轻一代的车主,尤其是年轻女性以及一些像袁毅这样的人,认为黑色的四门轿车“无聊”且“缺乏个性”。相反,他们在选择时强调“个性化”。然而,对老年人和中年专业人士来说,“没有屁股(后备箱)的轿车看起来很丑”。紧凑型轿车常常被打上某种烙印:如果车主买的紧凑型车属于低端品牌,就意味着车主买不起更大的轿车。如果小型车是大众甲壳虫或Mini Cooper,它可能被认为是富人的玩具,或是送给情人的礼物,或者是属于一个自我放纵的女人。一些访谈对象解释说,他们的偏好也是出于实用性的考虑。他们告诉我,政府喜欢使用某品牌的车是对其质量的一种认可。陆律师对于他为什么选择奥迪的说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迪要成为政府首选品牌,就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它不敢偷工减料。政府官员要求很高;他们的车必须安全且舒适。政府用它家的车,这在中国就是最好的广告和证明。陆律师的说法暗示了中国中产阶级经常体会到政府、市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虽然中产阶级拥护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让他们获得工作机会和随之而来的丰富商品,但他们对市场力量的道德性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政府是遏制市场中任何不道德行为的必要力量。“拥有和驾驶轿车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历史性的经验新兴的中产阶级为当代中国不断走高的轿车销售额提供了动力。然而,中产阶级对轿车的渴望不应该被简单地概括为消费主义所诱发的虚假意识,也不应该把他们对轿车便利性的论述仅仅看作是对虚荣心的修辞性伪装。在日常生活中,“拥有和驾驶轿车意味着什么”是一种历史性的经验。在美国,轿车被认为跨越阶级、性别和种族界限,是自由与自主的终极象征,这一观念深深植根于颂扬流动性和个人成就的美国主流文化中。然而,正如那培思所认为的,轿车和自由之间并没有内在的联系。在中国,买车开车的实践与这些实践所蕴含的意义环环相扣,它们受到各种社会进程的影响和塑造。正是在此过程结构中,是轿车本身,而不是轿车的价格,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轿车是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象征,社会地位向上流动是中产阶级强烈认同的一种价值观。在一个禁止个人拥有轿车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人,将拥有自己的轿车视作成功的标志。中产阶级通过别人的车来判断别人有多富裕,他们知道自己也处在同样的审视之下。虽然我的访谈对象们声称他们没有参与此类攀比,但他们都认为买车时应当选择“可以被人认出来的”的轿车品牌,且认为这一点很重要。然而,轿车作为社会地位的理想表现形式,并不仅仅是由其经济上的可承受性决定的。一方面,中产阶级承认轿车品牌对其社会地位的影响,但他们对豪华轿车品牌的态度却是模糊的。他们经常拿不同种类的高端轿车和它们的主人开玩笑,并指责新贵们玷污了这些品牌:奔驰和宝马同样都是为富人准备的,但后者往往与傲慢、粗暴、不负责任的新富为伍;而Mini Cooper和甲壳虫则被认为是情人专用。但许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承认,宝马是他们的梦想品牌,奥迪则是高质量轿车的代表。为了区别于那些喜欢通过玛莎拉蒂或跑车等豪车炫耀财富的新贵们,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强调,他们购买或喜欢奥迪等著名品牌,是因为工作需要或这些品牌的造车技术水准。当坐在一起讨论买哪辆车时,这些中产阶级专业人士(通常是男性)经常就各种(众所周知的名牌)轿车型号的工艺、经济、安全性能和美学设计进行激烈——甚至是竞争性的讨论。 电视剧《三十而已》(2020)剧照。另一方面,轿车的身份效应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复杂关系交织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社会环境下,中产阶级很多在年少时经历过“工作—家庭”空间移动模式,也经历过基础设施匮乏导致的空间流动性低下,对因为社会环境的种种限制而导致的社会流动性低下也有所理解。这些早年的记忆和对缺乏流动性的理解与中产阶层对轿车的渴望息息相关。集体实践也塑造了人们对某些事物和行动的特别感受力;轿车的身份效应也是如此。乘用车曾经仅用于公务。各种形式的轿车巡游到现在仍是表现声势的手段,影响着个人的审美经验。在这样的感知下,中产阶级通过轿车为物质媒介而共同分享某些实践和想象,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和团结性由此建立。那些为了休闲和娱乐而和朋友一起开车的人可能并不打算在朋友面前炫耀他们的成功,但许多坐在车里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同辈压力。在与朋友共进午餐、晚餐或周末出游时,车主可能会问那些没有车的人,他们准备什么时候买车,或者为什么没有买车。像董梅这样的人非常清楚哪些朋友或同事已经买了车,各是什么型号。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焦虑,还有渴望,渴望拥有和朋友及同龄人一样的生活方式。因此,轿车是识别他们同类人的工具,这些人共享一种独特的“工作—家庭”关系、生活节奏和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这种通过轿车获得并由轿车代表的新的流动性不可否认地给中产阶级带来了自由感。这种解放感类似于冰箱和洗衣机带来的解放感:这些技术发明使他们能够兼顾工作、家庭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不同需求和优先次序。轿车连接着空间、时间与人。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以前的生活经历、脑海挥之不去的画面和持续不断的盛大仪式仍对当代实践有着持久的影响。社会性扎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中,当中产阶级享受着轿车带来的控制感和流动性时,他们正在努力重构社会性。原文作者/张珺摘编/何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
电视剧《三十而已》(2020)剧照。另一方面,轿车的身份效应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复杂关系交织在一起。在20世纪90年代前的社会环境下,中产阶级很多在年少时经历过“工作—家庭”空间移动模式,也经历过基础设施匮乏导致的空间流动性低下,对因为社会环境的种种限制而导致的社会流动性低下也有所理解。这些早年的记忆和对缺乏流动性的理解与中产阶层对轿车的渴望息息相关。集体实践也塑造了人们对某些事物和行动的特别感受力;轿车的身份效应也是如此。乘用车曾经仅用于公务。各种形式的轿车巡游到现在仍是表现声势的手段,影响着个人的审美经验。在这样的感知下,中产阶级通过轿车为物质媒介而共同分享某些实践和想象,中产阶级的社会性和团结性由此建立。那些为了休闲和娱乐而和朋友一起开车的人可能并不打算在朋友面前炫耀他们的成功,但许多坐在车里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同辈压力。在与朋友共进午餐、晚餐或周末出游时,车主可能会问那些没有车的人,他们准备什么时候买车,或者为什么没有买车。像董梅这样的人非常清楚哪些朋友或同事已经买了车,各是什么型号。他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焦虑,还有渴望,渴望拥有和朋友及同龄人一样的生活方式。因此,轿车是识别他们同类人的工具,这些人共享一种独特的“工作—家庭”关系、生活节奏和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这种通过轿车获得并由轿车代表的新的流动性不可否认地给中产阶级带来了自由感。这种解放感类似于冰箱和洗衣机带来的解放感:这些技术发明使他们能够兼顾工作、家庭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不同需求和优先次序。轿车连接着空间、时间与人。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以前的生活经历、脑海挥之不去的画面和持续不断的盛大仪式仍对当代实践有着持久的影响。社会性扎根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社会规范和社会文化中,当中产阶级享受着轿车带来的控制感和流动性时,他们正在努力重构社会性。原文作者/张珺摘编/何也编辑/张进导语校对/赵琳 版权说明:
1.版权归本网站或原作者所有;
2.未经本网或原作者允许不得转载本文内容,否则将视为侵权;
3.转载或者引用本文内容请注明来源及原作者;
4.对于不遵守此声明或者其他违法使用本文内容者,本人依法保留追究权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