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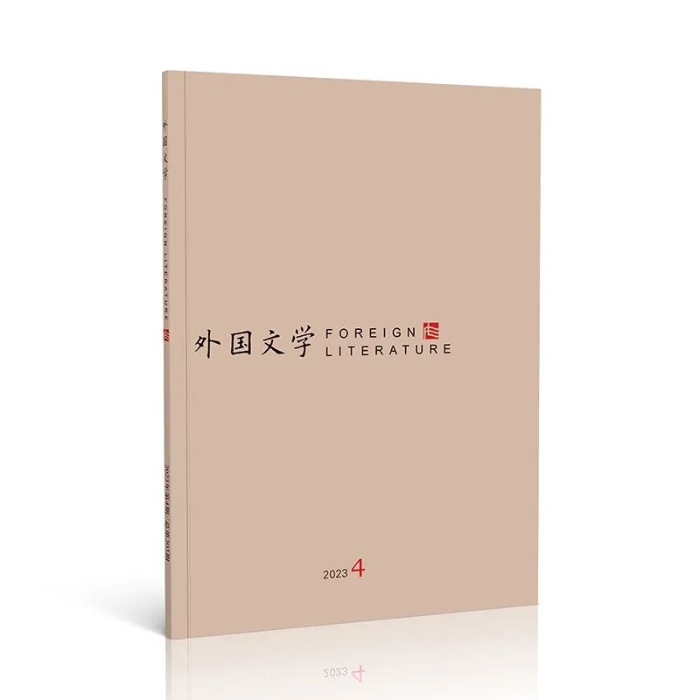
主 编: 金 莉
副主编:姜 红 马海良
风景
北京外国语大学 乔修峰
提要:
英语中的landscape(风景)最初指一个地方或一块土地;在文艺复兴时期词义发生了变化,开始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从“地方”到“景色”的这种转变,不仅是一种经由文化编码的再现过程,还将同一片土地分裂成了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导致了地方与其再现的分离,也凸显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风景研究开始反思风景概念的形成和嬗变,关注风景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问题,从生态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栖息地的关系,并借助中国的山水思想来弥补西方风景概念的局限。这些反思的意义在于,风景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和描述我们所处的世界,还关乎我们如何塑造这个世界。
关键词:
风景;观看;权力;生态;山水

略说
风景(Landscape)已经成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与空间、地方、自然、城乡、权力、记忆、身份、帝国、阶级、性别、生态等话题密切相关。当代的风景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艺术史和文化地理学曾是20 世纪风景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但当代的风景研究早已跨越了这两个学科的范畴。即便是传统的风景美学批评,也已经超越了绘画史,涵盖了诗学、小说、旅行文学和园艺等多个方面(Mitchell, “Imperial Landscape” 6)。多尔蒂(Gareth Doherty)和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主编的《风景是什么?》(Is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一书涉及十四个与风景相关的领域:文学、绘画、摄影、园林、生态、规划、城市设计、基础设施、科技、历史、理论、哲学、生活、建筑。面对风景如此多样的“身份”,穆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甚至在该书的前言中质疑道:“风景还是风景吗?”(xiv)
除了学科门类不易划分,风景概念本身也难以界定。历史地理学家迈尼格(Donald Meinig)认为,对于同一风景,十个人可能会有十种观看角度,分别把风景视为自然、栖息地、人造物、系统、问题、财富、意识形态、历史、地方、审美体验(“Beholding Eye” 33-48)。人文地理学家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甚至说:“风景无所不包——几乎囊括了我们周围的一切”(qtd. in Muir 5)。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也有不同的所指和表述。一般来说,“山水”(shan shui)多指自然风光,“风景”则兼顾自然和人文环境,而“景观”更偏重设计、建筑和地理。由于风景概念定义纷歧,有时为了表述精确,还会在它前面添加各种限定词,如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乡村风景与城市风景,等等,甚至还有政治景观等比喻用法(Antrop and Eetvelde“, Territory” 8)。
虽然具体所指驳杂不一,但西方的风景概念还是具有两层基本含义。它最初是指某个地方或一块土地,后来又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文艺复兴之后,后一种含义逐渐取代了前一种。这种词义的嬗变也影响了西方风景研究的历史,当代风景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趋势均与之密切相关。

词义的嬗变
英语中的landscape 是从欧洲西北部传入英国的外来词。对于该词进入英语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在中世纪,一种认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哈佛大学风景史教授斯蒂尔格(John R. Stilgoe)在《什么是风景?》(What Is Landscape?)一书中提出,该词是在16 世纪由弗里西亚语进入英语的,原文为landschop,指为抵御海水而修整的土地。当时的英国人把这个词错听或错说成了landskap 或landskep,后来又演变为landskip,最终变成了现在的landscape,指因人类居住而形成的地表部分(2-4)。美国乡土景观研究者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则认为,该词最早是在5 世纪时由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和其他日耳曼语系的群体传入英国的,land指一块有边界的空间,scape 相当于shape(形状),二者合在一起指土地的集合(13-16)。
虽然两人对“风景”一词进入英语的时间存在分歧,但都认为该词最初的含义是一块有人类活动的土地。不过,该词的含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强调土地的审美而非实用价值,突出视觉呈现,与绘画艺术关系密切。风景不仅有了“自然风光或风景画”这层含义,原有的“土地或地方”之义也开始淡化。历史学家沙玛(Simon Schama)在《风景与记忆》一书中认为,该词在荷兰更强调对土地的规划和利用,16 世纪传入英国后则多指值得描绘的景色(10)。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也曾指出:“最初,‘风景’一词主要涉及日常生活,指一块土地或一个地区。16世纪起,尤其是在荷兰和英国,风景越来越多地带有了美学意义,变成了一种艺术类型”(90)。地理学家安特罗普(Marc Antrop)在《风景研究简史》一文中虽然认为该词进入英语的时间是在17 世纪,但也认为它此时强调的是风光景致而非土地(1)。
《牛津英语大词典》(OED)的定义也印证了风景词义的上述变化。这部注重追溯词语历史的词典也强调,“风景”是在17 世纪作为绘画术语引入英国的,主要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在2006 年的一次研讨中,景观设计学者斯伯恩(Anne Whiston Spirn)认为这种界定抹杀了风景最初的含义,即一个地方以及在此地生活的人(qtd.in Deelue and Elkins 92)。风景史学者奥威格(Kenneth R. Olwig)认为,可能是因为《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编纂者发现了风景的两个基本含义之间差别过大,一个指具体地方,一个指绘画再现,便删除了前一个义项;不过,他发现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18 世纪编纂《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时,还保留着该词的两层含义:“1. 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景色;2. 一幅画,描绘一片空间,其中包含多种事物。”奥威格认为这两层含义实际上又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地方和景色,这是风景的两个核心层面,前者关乎“地方塑造”,后者涉及“空间审美”(“Actual Landscape”158-60)。
虽然约翰逊在他的词典中保留了风景的两层基本含义,但“自然风光或风景画”还是成了最常用的义项。也就是说,人们在谈论风景时,更多涉及“空间审美”而非“地方塑造”。奥威格在《风景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Landscape)一书中将这种变化归纳为从“地方和共同体”到“景色空间”的转变(7),这是一种从现实到再现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风景画是一种再现,景色本身也是一种再现,二者都属于对地方的再现。如米切尔(W. J. T. Mitchell)所说,景色属于对地方的第一层再现,风景画则是对这种再现的再现,属于次级再现(“Imperial Landscape” 14)。不过,很多学者认为,“风景画”这个义项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景色或“自然风光”。奥威格从语义层面进行了溯源,认为“风景”在文艺复兴时期先是指“一幅描绘内陆自然风光的画作”,后来才渐渐开始指现实中像风景画那样的景色(Meanings 8-9)。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的艺术史考证也佐证了这一点,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和风景画的兴起》一文中提出,在16 世纪的意大利,先有了“风景画”的概念,才形成了风景画市场,进而推动风景画发展成为单独的画种,并影响了人们对风景的感知(132, 142)。在他们看来,人们对自然风光的审美,实际上是先受到了风景画的概念和绘画模式的影响。
关于风景概念的起源和嬗变,上述观点是目前学界的主流声音,但也并非没有质疑之声。法国地理学家边留久(Augustin Berque)就认为,当人们说风景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时,实际上指的是关于风景的思考,这种思考需要借助语言,应当被称作“风景理论”(landscape theory);而“风景文化”(landscape thinking)并不一定需要语言,文艺复兴之前没有风景理论,但并不能说那时候的人不会欣赏风景,他们也有自己认识风景的方式,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景文化。在他看来,恰恰是风景理论排斥了风景文化(3-4)。不过,20 世纪下半叶之后,边留久所说的“风景理论”也在反思风景的词义嬗变引出的问题。一方面,“自然风光或风景画”作为“土地或地方”的再现,已经经过了意识形态的编码,隐含着权力关系;另一方面,风景的审美意义凸显,将“地方”客体化,影响了人们对人与栖息地关系的认识。

观看与权利
地理学者安特罗普(Marc Antrop)和埃特维尔德(Veerle Van Eetvelde)在《风景视角》(Landscape Perspectives)一书中总结了西方风景研究的历史。他们认为,西方的风景研究兴起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代,在19世纪之前主要是描绘、想象和设计风景,19世纪至20 世纪初有了地理学的参与,20 世纪以来更是呈现出跨学科的特征(12)。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的风景研究经历过两次重要的转向。米切尔认为,第一次转向与现代主义有关,主要是根据风景画的历史来理解风景的历史,如贡布里希的文章《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和风景画的兴起》;第二次则与后现代主义有关,转向了符号学和阐释学方法,把风景视为心理或意识形态主题的一种寓言(Introduction 1)。显然,第二次转向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学界日益重视语言、意义、再现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作用有关。
文化地理学家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认为,英语中将风景定义为从某一点看到的一片土地,这个观看地点使观者享有一种特权,可以选择、框定、组合自己的所见,用想象力将物质空间转换为风景(“Landscape” 254)。这种转换以观看(seeing)为媒介,而观看又必然受观看者的思想框架和文化背景制约。如迈尼格所说:“风景是由我们的视野来界定的,并由我们的头脑来解释”(Introduction 3);或如沙玛所言:“在感官接触风景之前,风景就已经在脑中了。景色是从一层层的记忆中构建出来的,这些记忆就像一层层的岩石一样”(6-7)。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总会有所选择,而且只能看到我们头脑或记忆中已有的东西。有鉴于此,科斯格罗夫借用伯格(John Berger)在1969 年提出的观点,不再把风景视为单纯的目光所见,而是一种包含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观看方式”(Social Formation 13;“ Landscape” 252)。
风景作为“观看方式”,涉及谁在看、在哪儿看、看到什么,而这些问题又关乎权力关系或意识形态问题。米切尔在《神圣的风景: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美国荒野》一文中指出:
主导了西方艺术史的风景概念,一直以视觉再现和图像再现为中心,即再现自然地表秀丽的、如画的、表面的样子。风景可以观看,但无法触及。它是地方的抽象化,空间的具体化。它被削减为从一定距离之外的视点看到的东西。这样一种远眺,借助一套相对可预见的传统——诗意的、如画的、崇高的、田园的等等——控制了风景,将风景框定起来,给风景编码。(265)也就是说,作为自然风光或风景画的风景,在经过文化的编码之后,将现实的“地方”转换成了再现的“空间”,从而掩盖或支持某种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抹杀或改写地方的历史,还会将这种行为隐藏起来或者使之合理化。如米切尔所言,描绘出来的风景“不仅仅是自然景色,也不仅仅是自然景色的再现,而是把这种对自然景色的再现变得如同天然而成”(“Imperial Landscape” 15)。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景不仅表征权力关系,而且是文化权力的工具(Introduction 1-2)。
达比(Wendy Joy Darby)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中提出,描绘某地的风景和“命名、制图、测量、居住”一样,都是一种权力施为,是“将空间殖民化”(50)。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帝国和阶级两个方面。奥威格认为,对“帝国风景”的描绘,可以通过有选择地呈现殖民地空间,否认或改写该地的文化和原住民(“Actual Landscape” 175)。例如,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19 世纪欧洲人写的非洲游记中发现,很多风景描写都“将当地居民与其所居之地分割开来”(126)。萨义德(Edward Said)也在《虚构、记忆和地方》一文中谈到,“一个地方的地理可以被改写、虚构和描绘,完全远离该地的实际情况”;“犹太复国主义就利用虚构的记忆,清空了巴勒斯坦的居民和历史,将该地的风景变为空无一物的空间”(246, 254)。早在其《东方学》(Orientalism)中,萨义德就探讨过虚构和建构出来的地理空间可以无视真实的地方,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和霸权关系(5)。
米切尔认为,帝国风景并不只是由本土向外扩张,也会反过来重新塑造本土。在他看来,英国近代的圈地运动,就是本土内部的殖民,使绿色的田野变成风景,从而成为民族和帝国身份的象征(“Imperial Landscape” 9, 17)。这种将本土地方变成风景的过程,掩盖了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英国18、19 世纪风景画中的青葱绿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想象和建构,用虚假的宁静祥和掩盖乡村劳动者的艰辛和乡村的阶级矛盾。艺术史学者伯明翰(Ann Birmingham)认为,英国18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如画”(picturesque)美学就是“试图抹去圈地运动的事实,并将其影响最小化”(75)。如画美学在赋予某个地方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抹去了劳动的痕迹。劳动者即便出现在视野中,也不过是点景人物。这实际上是用美学来掩盖政治、经济和道德问题。罗斯金(John Ruskin)在19 世纪中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现代画家》中说:“在小溪转弯处,我看到一个人在钓鱼,旁边有一个男孩和一只狗——这当然很如画,很悦目,如果他们没有一整天都在饿肚子的话”(269)。巴瑞尔(John Barrell)做了更为详尽的研究,他在《风景中的阴暗面:1730—1840 年间英国绘画中的乡村穷人》中考察了风景画中“穷人是如何被再现的(不如说是如何不被再现的)”,认为风景的再现不仅涉及审美,还涉及道德和社会问题(1)。
将地方再现为风景,在美学上是一种选择性的观看方式,在政治上则是一种排斥性的观看方式,同一片土地被分裂为“地方”和“景色”,也就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区分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对于在土地上劳动的农夫来说,土地就是生产空间;但对于欣赏自然风光的农业资产阶级来说,土地却主要是一种消费空间。这种空间的分裂不仅呼应了风景概念两层基本含义的分离,也体现着不同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18 世纪英国的土地所有者或农业资产阶级一方面靠作为生产空间的土地为生,剥削在土地上劳作的佃农;另一方面又通过建造宅邸和庭园,从视觉上排除谷仓、磨坊、农夫等“生产事实”,营造出一种没有农业劳动和农夫的“风景”,虚构了一个“未被破坏的”自然。农业资产阶级从自己乡宅的窗口、露台、草坪上俯视或远眺自己的土地,是一种审美的而非实用的观看方式,但这种观看又是以占有和控制土地为基础的(154-55)。即便观景者是游客而非这片土地的所有者,也不影响威廉斯观点的成立,因为在19 世纪中叶由铁路推动的大众旅游兴起之前,大部分游客都是从土地中获利的群体。如果说威廉斯区分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在18、19 世纪的英国主要涉及阶级问题,在20 世纪之后则更多涉及人的存在问题,也就是人与栖息地的关系问题。

4. 人与栖息地
如果风景仅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就印证了威廉斯的那句名言:“风景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分离与观看”(265);观看风景的人,始终是从一定的距离之外欣赏风景。科斯格罗夫把观景的人称作“外部人”(outsider),而以土地为生计和家园的人无法与土地分离,属于“内部人”(insider),土地对他们而言主要是地方而不是景色(Social Formation 19)。对于同一片土地,“外部人”看到了景色,却不属于这个地方,这里对他来说是消费空间;而“内部人”虽然属于这个地方,却又看不到景色,这里对他来说只是生产空间。这也就意味着当风景仅指自然风光而非地方时,人就无法“属于”风景。这种由概念引起的悖论显然影响了人们对人与栖息地关系的认识。随着20 世纪70 年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有学者主张将风景概念的两层基本含义“地方”和“景色”,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侧重分离和观看转向强调关联和体验。
马尔帕斯(Jeff Malpas)在《地方与风景问题》一文中反对将风景分为“生活的”(lived)和“再现的”(represented)两个层面,因为在再现地方之前,人们就已经与地方发生了关系:“只有在我们与地方产生了关系之后,风景才会出现。那个地方通过它的声音、气味、情感和景色影响了我们,而且可以说,是通过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行动影响了我们,我们也因此在那个地方发现了自己”(11, 13) 。在他看来,“风景无论是作为生活的地方,还是作为再现的作品,总涉及积极的参与和体验”(19),而自我也正是在这种参与和体验中形成的:“风景可能是在人的干预下形成的,但人自身一定是风景塑造的。在这种关系中,没有哪一方占据上风——双方都在影响并适应对方”(17)。当我们不再把风景分裂为地方和景色的时候,风景也就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成了我们赖以形成的东西。人与风景的关系也就不再是分离,而是关联。
哈佛大学摄影学教授凯尔西(Robin Kelsey)发现,当代的风景研究格外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但他认为现在有必要“从强调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转向强调物种与栖息地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204)。他在《侧身风景之外》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采取的是一种凌驾于风景之上的态度,认为风景属于我们,但我们不属于风景。这其实是“一种幻想,幻想自己不属于一片土地上的总体生活”(204)。其根源就在于把“地方”与“景色”分离开了,也就是马尔帕斯所说的将风景分为“生活的”和“再现的”,或威廉斯所说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凯尔西承认,现代人在审美上渴望能够融入风景。例如,有浪漫情怀的人渴望能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有怀旧情愫的人认为我们曾经是风景的一部分,并渴望能够再度回到风景之中。但问题在于,这两种渴望的前提都是认为自己并不属于风景(208)。从生态的角度看,“不属于风景”实际上只是人们的幻想,但要打破这种幻想,重新回到风景之中,又意味着限制和责任,意味着要使人类与其他物种平起平坐。凯尔西认为,这种生态视角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行合一。他举例说,人们现在或许不难认识到自己的一些消费方式,如乘坐飞机和使用空调,可能会影响全球气候,但是否愿意因此而放弃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舒适和便捷,就不一定了(210)。这也是一个亟待我们思考和应对的问题,因为保护环境实质上是保护人类自身。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真正面临危险的不是地球,而是人类的未来,人们现在需要走出我们能够保护自然的“迷思”(156)。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风景是什么的认识,也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风景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要寻求二者的关联和交融,不仅需要弥合风景的两层基本含义之间的鸿沟,还要进一步整合风景研究的不同路径。这一点也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风景的研究历史来看,风景的两层含义带来了看待风景的两大角度,即段义孚所说的“功能性的”和“道德—审美的”角度(89-90);后者将风景视为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关注风景是如何被感知、阐释和再现的。怀特(Ian D. Whyte)在《16 世纪以来的风景与历史》中认为,这是一种主观的研究方法,代表人物有阿普尔顿(Jay Appleton)、科斯格罗夫、米切尔、伯格等。怀特认为西方的风景研究还有一种客观的方法,关注自然与人类力量在一段时间内对风景的改变,代表人物有历史学家霍斯金斯(W. G. Hoskins)、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等(15-26)。这两种方法在20 世纪的风景研究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特罗普和埃特维尔德认为,现在有必要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因为风景“从各种比例和各种层面,融合了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美学、地理与历史、人类与环境。风景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的地方,是空间与时间交汇的地方”(4)。面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建构一种整体的(holistic)风景观显得尤为迫切。这种风景观不再区分“地方”与“景色”,而是将二者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改变我们对人与栖息地关系的认识,进而改变我们的存在状态。

从风景到山水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风景概念主要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实际上是将风景视为客体,而作为主体的我们则侧身风景之外。如沃勒克(Alan Wallach)所言,西方风景传统的核心就是一种建立在“我—它”、自我与他者、观者与被观者基础上的主体—客体关系(317)。这种强调分离与观看的风景传统显然不利于人与栖息地的交融。近年来,以法国汉学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和地理学家边留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尝试借鉴中国的山水思想,消除西方风景概念中隐含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把风景视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或资源。
朱利安在《山水之间,或理性的未思》(Living Off Landscape or the Unthought-of in Reason)中提出,“风景”是典型的欧洲词语,如弗莱芒语中的landschap、德语中的Landschaft、英语中的landscape、法语中的paysage、意大利语中的paesaggio、西班牙语中的paisaje、俄语中的пейзаж(2)。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词汇,如“山水”和“风景”。“山水”原指山和水两种地理形态,或山中之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渐渐开始指由丘石林泉构成的优美环境,由地理词汇变成了美学词汇。中文中的“风景”一词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指风光景致。相对而言,“山水”使用的频率更高,也一直是中国风景的主体(吴静子、王其亨 29-47;刘洁 11-12)。不过,无论是中文中的“风景”还是“山水”,都不像西方的风景概念那样凸显观者与景色、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宗白华在分析中西风景画法的不同境界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123)。
朱利安认为欧洲的风景概念存在三大偏见:一是忽视整体,将风景当作观者的目光从大地上剪裁出的“一部分”;二是过于强调视觉,将观看当作进入风景的唯一方式;三是主体与客体分离,将观者与大自然对立起来(Living Off 5)。第一个偏见使风景拘囿于目光所及之处,并将目光所框定的这部分土地抽象为一个均质的几何空间,抹杀了土地的个性;第二个偏见把风景减缩为表象,并使观者脱离了听觉和味觉等感觉所依赖的环境氛围;第三个偏见不仅使人与世界对立起来,还使人与世界分离开来(7-9)。
显然,这三个偏见都与观看有关,朱利安对欧洲风景概念的修正也是由此入手。他认为第一应该区分“风景”(landscape)和“所见之景”(view)。“所见之景”是将视线投向客体,有一个固定的焦点;而“风景”需要使目光移动起来,不受固定焦点的束缚。第二应该区分“用眼睛看”(with my eyes)和“通过眼睛去看”(through my eyes):对前者而言,眼睛是使动者,是主体在观察事物,通过视线来描述客体;而对于后者,眼睛只是中介,主体不是在看“什么”,而是在看,目光不再固定,而是游移于事物之间,风景也由是进入了观者的内心——观察(observe)变成了静观(contemplate; 10-14)。
朱利安发现中国的山水观有助于纠正欧洲风景概念的上述偏颇。欧洲人将风景视为视线从大地上剪裁出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山水则强调“山”和“水”这组对立事物的关联。山水包含了高低、纵横、静动、常变、虚实、有形与无形、不透明与透明。山与水的两极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的存在有赖于另一方。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呈现在眼前的大自然,因为大自然乃是两极之间的互动;也没有了独立于风景之外的观者,因为观者就在山与水之间,在山水之内(Living Off 15-16)。
朱利安还发现,中国的山水画与西方的风景画也反映了上述不同。北宋画家郭熙在其画论《山水训》中提出了山有“三远”之说:“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51)。朱利安认为,高远、深远、平远分别对应着仰、窥、望三种观看方式,强调视线的移动,可以组织出多重视角,不像西方风景画那样固定在一个观察点、集中在一个焦点观看(Living Off 34-35)。郭熙还提出,“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40)。朱利安认为,虽然可行和可望涉及客体和距离,但可居强调风景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人类生活的环境。因此,山水的价值不在于审美(强调分离、客体、观看),而在于滋养生命(强调身处其中、交融、生活;Living Off 36-40)。如此一来,风景便“不再只是被‘观看’或‘再现’,而是与生命联系在了一起”;“不再像通常所定义的那样,是大自然‘呈现’给‘观者’的大地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生活可以无限汲取的资源”(x)。
朱利安还在《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一书中解释了中国的山水思想何以能打破西方风景概念的主客体之分。一方面,他援引苏东坡的名句“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来说明山水“大象无形”(山水画也因此追求传神而不求形似),乃是两极之间的互动和无穷交会,包含了一切使万物富有生机的东西,因而无法被客体化(278-79, 259-61);另一方面,他又援引石涛的名句“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来说明人与山水同源,都是“气”的产物,山水与人乃是伙伴关系,也就无所谓主客体之分(279-82)。关于第二个方面,朱利安还借用南朝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山水“质有而趣灵”一说,认为山水兼具物质(质有)与精神(趣灵)特性。这两种特性之间并没有裂隙,因为山水散发着气韵(aura),而气韵既不属于形体也不属于神灵,既不属于可见也不属于不可见,而是将二者笼罩在了一起(Living Off 59, 63)。边留久也意识到宗炳所说的“质有而趣灵”已经指出了山水的两面性:一面是“物质的、可见的事物”,一面是“非物质的、不可见的关系”(45)。在他看来,西方将风景视为客体,也就抹杀了“趣灵”,“导致了风景的消亡”(51)。因此,他认为“发明风景”这个说法并不恰当,是在强调风景只是人类目光凝视的产物;应该说“风景的诞生”,因为“风景并非存在于对客体的凝视之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之中,换言之,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与环境的关系之中”(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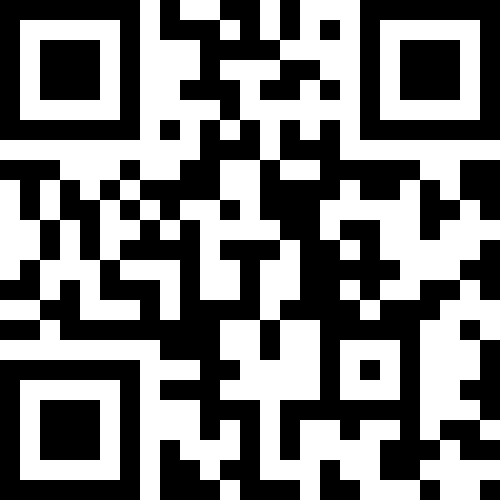
本文发表于《外国文学》2023年第4期,更多文章信息
请扫描上方二维码或复制链接(https://sourl.cn/mAYGN2)到浏览器,移步知网下载
期
刊
在线阅读及其下载
在学术期刊官网,阅读全文
https://www.bfsujournals.com/c/2019-07-18/486526.shtml
在知网下载期刊全文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tYqgYjzYKsDSiPqMb_JlxDh5l_G-6d0jvyMO5rJ0Jy2VngJdW87prC6pL7TTDlx_75CfRWNj8tHTfLC5tvzHi_fEAaxme6iwD5SOmK6Kh5Qeveorb01GLA==&uniplatform=NZK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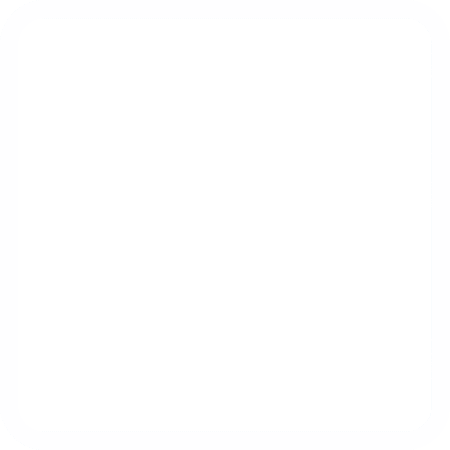
期刊介绍
本刊创办于1980年,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刊物之一,主要栏目包括评论、理论、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书评等。
荣誉及数据库收录: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数据库收录,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22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和“2018最受学界欢迎的20种学术期刊(人文学科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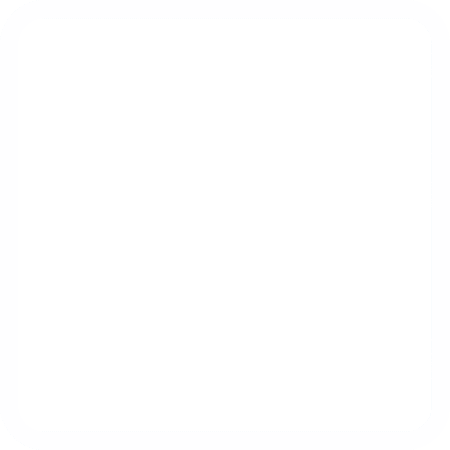
期刊订阅方式
中国邮政订阅:
邮发代码:2-450
国内统一刊号:CN11-1248/I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5529
1、各地邮局期刊征订处
2、订阅拨打中国邮政官方电话11185订阅
淘宝、天猫电商销售:
单期购买。通过外研社天猫旗舰店购买当期以及过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id=731796377346&rn=cf22f10704b9d5b494022dc143078467&spm=a1z10.3-b-s.w4011-22665586135.102.779137e9NOmEly&skuId=5070249833617
往期精选
外国文学 | 论中世纪英国的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文/李维屏)
外国文学 | 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悖论(文/赵 淳)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5期目录及摘要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4期目录及摘要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3期目录及摘要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外国文学| 西方文论关键词:新物质主义(文/韩启群)
刊讯 | 《外国文学》(2023年第1期)目录及其摘要
外国文学| 西方文论关键词:非个人化(文/许小凡)
刊讯| 《外国文学》2022年第六期目录及其摘要
重磅通知︱必看的11本优秀学术期刊
外国文学 | 诗人、超灵与“解救万物的诸神” ——爱默生论莎士比亚及其内在悖论
期刊概览:《外国文学》(2022年第5期)目录及其摘要
《外国文学》编辑部召开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与阐释”工作推进会
外国文学 | 西方文论关键词:接受美学(文/任卫东)
祝贺《外国文学》进入文学类学术期刊Q1区!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
转载请注明来自微信订阅号:北外学术期刊
北外学术期刊官网:https://www.bfsujournals.com/
欢迎分享与转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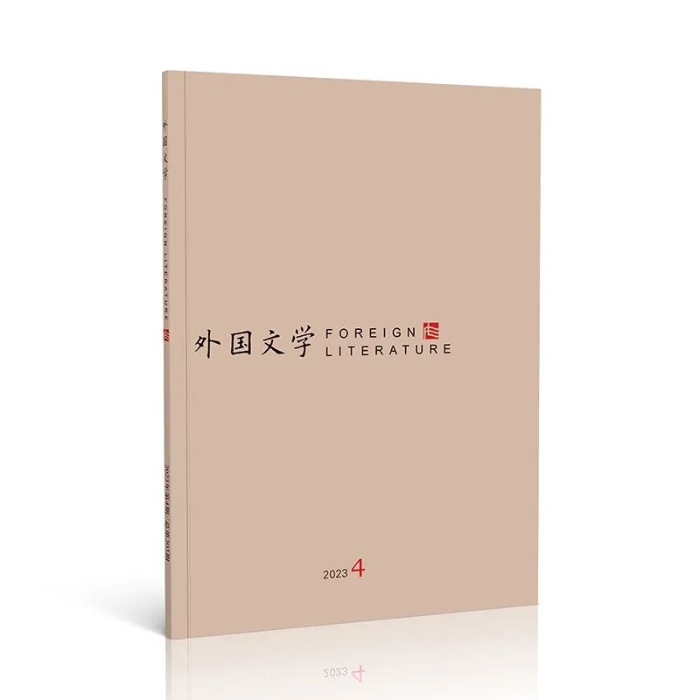 主 编: 金 莉
副主编:姜 红 马海良
风景
北京外国语大学 乔修峰
提要:
英语中的landscape(风景)最初指一个地方或一块土地;在文艺复兴时期词义发生了变化,开始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从“地方”到“景色”的这种转变,不仅是一种经由文化编码的再现过程,还将同一片土地分裂成了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导致了地方与其再现的分离,也凸显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风景研究开始反思风景概念的形成和嬗变,关注风景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问题,从生态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栖息地的关系,并借助中国的山水思想来弥补西方风景概念的局限。这些反思的意义在于,风景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和描述我们所处的世界,还关乎我们如何塑造这个世界。
关键词:
风景;观看;权力;生态;山水
主 编: 金 莉
副主编:姜 红 马海良
风景
北京外国语大学 乔修峰
提要:
英语中的landscape(风景)最初指一个地方或一块土地;在文艺复兴时期词义发生了变化,开始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从“地方”到“景色”的这种转变,不仅是一种经由文化编码的再现过程,还将同一片土地分裂成了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导致了地方与其再现的分离,也凸显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的风景研究开始反思风景概念的形成和嬗变,关注风景中隐含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问题,从生态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栖息地的关系,并借助中国的山水思想来弥补西方风景概念的局限。这些反思的意义在于,风景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不仅关乎我们如何理解和描述我们所处的世界,还关乎我们如何塑造这个世界。
关键词:
风景;观看;权力;生态;山水
 略说
风景(Landscape)已经成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与空间、地方、自然、城乡、权力、记忆、身份、帝国、阶级、性别、生态等话题密切相关。当代的风景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艺术史和文化地理学曾是20 世纪风景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但当代的风景研究早已跨越了这两个学科的范畴。即便是传统的风景美学批评,也已经超越了绘画史,涵盖了诗学、小说、旅行文学和园艺等多个方面(Mitchell, “Imperial Landscape” 6)。多尔蒂(Gareth Doherty)和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主编的《风景是什么?》(Is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一书涉及十四个与风景相关的领域:文学、绘画、摄影、园林、生态、规划、城市设计、基础设施、科技、历史、理论、哲学、生活、建筑。面对风景如此多样的“身份”,穆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甚至在该书的前言中质疑道:“风景还是风景吗?”(xiv)
除了学科门类不易划分,风景概念本身也难以界定。历史地理学家迈尼格(Donald Meinig)认为,对于同一风景,十个人可能会有十种观看角度,分别把风景视为自然、栖息地、人造物、系统、问题、财富、意识形态、历史、地方、审美体验(“Beholding Eye” 33-48)。人文地理学家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甚至说:“风景无所不包——几乎囊括了我们周围的一切”(qtd. in Muir 5)。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也有不同的所指和表述。一般来说,“山水”(shan shui)多指自然风光,“风景”则兼顾自然和人文环境,而“景观”更偏重设计、建筑和地理。由于风景概念定义纷歧,有时为了表述精确,还会在它前面添加各种限定词,如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乡村风景与城市风景,等等,甚至还有政治景观等比喻用法(Antrop and Eetvelde“, Territory” 8)。
虽然具体所指驳杂不一,但西方的风景概念还是具有两层基本含义。它最初是指某个地方或一块土地,后来又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文艺复兴之后,后一种含义逐渐取代了前一种。这种词义的嬗变也影响了西方风景研究的历史,当代风景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趋势均与之密切相关。
略说
风景(Landscape)已经成了文学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热点,与空间、地方、自然、城乡、权力、记忆、身份、帝国、阶级、性别、生态等话题密切相关。当代的风景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征。艺术史和文化地理学曾是20 世纪风景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但当代的风景研究早已跨越了这两个学科的范畴。即便是传统的风景美学批评,也已经超越了绘画史,涵盖了诗学、小说、旅行文学和园艺等多个方面(Mitchell, “Imperial Landscape” 6)。多尔蒂(Gareth Doherty)和瓦尔德海姆(Charles Waldheim)主编的《风景是什么?》(Is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Identity of Landscape)一书涉及十四个与风景相关的领域:文学、绘画、摄影、园林、生态、规划、城市设计、基础设施、科技、历史、理论、哲学、生活、建筑。面对风景如此多样的“身份”,穆斯塔法维(Mohsen Mostafavi)甚至在该书的前言中质疑道:“风景还是风景吗?”(xiv)
除了学科门类不易划分,风景概念本身也难以界定。历史地理学家迈尼格(Donald Meinig)认为,对于同一风景,十个人可能会有十种观看角度,分别把风景视为自然、栖息地、人造物、系统、问题、财富、意识形态、历史、地方、审美体验(“Beholding Eye” 33-48)。人文地理学家洛温塔尔(David Lowenthal)甚至说:“风景无所不包——几乎囊括了我们周围的一切”(qtd. in Muir 5)。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也有不同的所指和表述。一般来说,“山水”(shan shui)多指自然风光,“风景”则兼顾自然和人文环境,而“景观”更偏重设计、建筑和地理。由于风景概念定义纷歧,有时为了表述精确,还会在它前面添加各种限定词,如自然景观与文化景观、乡村风景与城市风景,等等,甚至还有政治景观等比喻用法(Antrop and Eetvelde“, Territory” 8)。
虽然具体所指驳杂不一,但西方的风景概念还是具有两层基本含义。它最初是指某个地方或一块土地,后来又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文艺复兴之后,后一种含义逐渐取代了前一种。这种词义的嬗变也影响了西方风景研究的历史,当代风景研究中的几个重要趋势均与之密切相关。 词义的嬗变
英语中的landscape 是从欧洲西北部传入英国的外来词。对于该词进入英语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在中世纪,一种认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哈佛大学风景史教授斯蒂尔格(John R. Stilgoe)在《什么是风景?》(What Is Landscape?)一书中提出,该词是在16 世纪由弗里西亚语进入英语的,原文为landschop,指为抵御海水而修整的土地。当时的英国人把这个词错听或错说成了landskap 或landskep,后来又演变为landskip,最终变成了现在的landscape,指因人类居住而形成的地表部分(2-4)。美国乡土景观研究者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则认为,该词最早是在5 世纪时由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和其他日耳曼语系的群体传入英国的,land指一块有边界的空间,scape 相当于shape(形状),二者合在一起指土地的集合(13-16)。
虽然两人对“风景”一词进入英语的时间存在分歧,但都认为该词最初的含义是一块有人类活动的土地。不过,该词的含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强调土地的审美而非实用价值,突出视觉呈现,与绘画艺术关系密切。风景不仅有了“自然风光或风景画”这层含义,原有的“土地或地方”之义也开始淡化。历史学家沙玛(Simon Schama)在《风景与记忆》一书中认为,该词在荷兰更强调对土地的规划和利用,16 世纪传入英国后则多指值得描绘的景色(10)。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也曾指出:“最初,‘风景’一词主要涉及日常生活,指一块土地或一个地区。16世纪起,尤其是在荷兰和英国,风景越来越多地带有了美学意义,变成了一种艺术类型”(90)。地理学家安特罗普(Marc Antrop)在《风景研究简史》一文中虽然认为该词进入英语的时间是在17 世纪,但也认为它此时强调的是风光景致而非土地(1)。
《牛津英语大词典》(OED)的定义也印证了风景词义的上述变化。这部注重追溯词语历史的词典也强调,“风景”是在17 世纪作为绘画术语引入英国的,主要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在2006 年的一次研讨中,景观设计学者斯伯恩(Anne Whiston Spirn)认为这种界定抹杀了风景最初的含义,即一个地方以及在此地生活的人(qtd.in Deelue and Elkins 92)。风景史学者奥威格(Kenneth R. Olwig)认为,可能是因为《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编纂者发现了风景的两个基本含义之间差别过大,一个指具体地方,一个指绘画再现,便删除了前一个义项;不过,他发现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18 世纪编纂《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时,还保留着该词的两层含义:“1. 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景色;2. 一幅画,描绘一片空间,其中包含多种事物。”奥威格认为这两层含义实际上又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地方和景色,这是风景的两个核心层面,前者关乎“地方塑造”,后者涉及“空间审美”(“Actual Landscape”158-60)。
虽然约翰逊在他的词典中保留了风景的两层基本含义,但“自然风光或风景画”还是成了最常用的义项。也就是说,人们在谈论风景时,更多涉及“空间审美”而非“地方塑造”。奥威格在《风景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Landscape)一书中将这种变化归纳为从“地方和共同体”到“景色空间”的转变(7),这是一种从现实到再现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风景画是一种再现,景色本身也是一种再现,二者都属于对地方的再现。如米切尔(W. J. T. Mitchell)所说,景色属于对地方的第一层再现,风景画则是对这种再现的再现,属于次级再现(“Imperial Landscape” 14)。不过,很多学者认为,“风景画”这个义项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景色或“自然风光”。奥威格从语义层面进行了溯源,认为“风景”在文艺复兴时期先是指“一幅描绘内陆自然风光的画作”,后来才渐渐开始指现实中像风景画那样的景色(Meanings 8-9)。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的艺术史考证也佐证了这一点,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和风景画的兴起》一文中提出,在16 世纪的意大利,先有了“风景画”的概念,才形成了风景画市场,进而推动风景画发展成为单独的画种,并影响了人们对风景的感知(132, 142)。在他们看来,人们对自然风光的审美,实际上是先受到了风景画的概念和绘画模式的影响。
关于风景概念的起源和嬗变,上述观点是目前学界的主流声音,但也并非没有质疑之声。法国地理学家边留久(Augustin Berque)就认为,当人们说风景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时,实际上指的是关于风景的思考,这种思考需要借助语言,应当被称作“风景理论”(landscape theory);而“风景文化”(landscape thinking)并不一定需要语言,文艺复兴之前没有风景理论,但并不能说那时候的人不会欣赏风景,他们也有自己认识风景的方式,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景文化。在他看来,恰恰是风景理论排斥了风景文化(3-4)。不过,20 世纪下半叶之后,边留久所说的“风景理论”也在反思风景的词义嬗变引出的问题。一方面,“自然风光或风景画”作为“土地或地方”的再现,已经经过了意识形态的编码,隐含着权力关系;另一方面,风景的审美意义凸显,将“地方”客体化,影响了人们对人与栖息地关系的认识。
词义的嬗变
英语中的landscape 是从欧洲西北部传入英国的外来词。对于该词进入英语的时间,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在中世纪,一种认为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哈佛大学风景史教授斯蒂尔格(John R. Stilgoe)在《什么是风景?》(What Is Landscape?)一书中提出,该词是在16 世纪由弗里西亚语进入英语的,原文为landschop,指为抵御海水而修整的土地。当时的英国人把这个词错听或错说成了landskap 或landskep,后来又演变为landskip,最终变成了现在的landscape,指因人类居住而形成的地表部分(2-4)。美国乡土景观研究者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则认为,该词最早是在5 世纪时由盎格鲁人、撒克逊人、朱特人、丹麦人和其他日耳曼语系的群体传入英国的,land指一块有边界的空间,scape 相当于shape(形状),二者合在一起指土地的集合(13-16)。
虽然两人对“风景”一词进入英语的时间存在分歧,但都认为该词最初的含义是一块有人类活动的土地。不过,该词的含义在文艺复兴时期已经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强调土地的审美而非实用价值,突出视觉呈现,与绘画艺术关系密切。风景不仅有了“自然风光或风景画”这层含义,原有的“土地或地方”之义也开始淡化。历史学家沙玛(Simon Schama)在《风景与记忆》一书中认为,该词在荷兰更强调对土地的规划和利用,16 世纪传入英国后则多指值得描绘的景色(10)。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也曾指出:“最初,‘风景’一词主要涉及日常生活,指一块土地或一个地区。16世纪起,尤其是在荷兰和英国,风景越来越多地带有了美学意义,变成了一种艺术类型”(90)。地理学家安特罗普(Marc Antrop)在《风景研究简史》一文中虽然认为该词进入英语的时间是在17 世纪,但也认为它此时强调的是风光景致而非土地(1)。
《牛津英语大词典》(OED)的定义也印证了风景词义的上述变化。这部注重追溯词语历史的词典也强调,“风景”是在17 世纪作为绘画术语引入英国的,主要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在2006 年的一次研讨中,景观设计学者斯伯恩(Anne Whiston Spirn)认为这种界定抹杀了风景最初的含义,即一个地方以及在此地生活的人(qtd.in Deelue and Elkins 92)。风景史学者奥威格(Kenneth R. Olwig)认为,可能是因为《牛津英语大词典》的编纂者发现了风景的两个基本含义之间差别过大,一个指具体地方,一个指绘画再现,便删除了前一个义项;不过,他发现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18 世纪编纂《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时,还保留着该词的两层含义:“1. 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景色;2. 一幅画,描绘一片空间,其中包含多种事物。”奥威格认为这两层含义实际上又可以归纳为两个层面:地方和景色,这是风景的两个核心层面,前者关乎“地方塑造”,后者涉及“空间审美”(“Actual Landscape”158-60)。
虽然约翰逊在他的词典中保留了风景的两层基本含义,但“自然风光或风景画”还是成了最常用的义项。也就是说,人们在谈论风景时,更多涉及“空间审美”而非“地方塑造”。奥威格在《风景的意义》(The Meanings of Landscape)一书中将这种变化归纳为从“地方和共同体”到“景色空间”的转变(7),这是一种从现实到再现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不仅风景画是一种再现,景色本身也是一种再现,二者都属于对地方的再现。如米切尔(W. J. T. Mitchell)所说,景色属于对地方的第一层再现,风景画则是对这种再现的再现,属于次级再现(“Imperial Landscape” 14)。不过,很多学者认为,“风景画”这个义项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景色或“自然风光”。奥威格从语义层面进行了溯源,认为“风景”在文艺复兴时期先是指“一幅描绘内陆自然风光的画作”,后来才渐渐开始指现实中像风景画那样的景色(Meanings 8-9)。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的艺术史考证也佐证了这一点,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和风景画的兴起》一文中提出,在16 世纪的意大利,先有了“风景画”的概念,才形成了风景画市场,进而推动风景画发展成为单独的画种,并影响了人们对风景的感知(132, 142)。在他们看来,人们对自然风光的审美,实际上是先受到了风景画的概念和绘画模式的影响。
关于风景概念的起源和嬗变,上述观点是目前学界的主流声音,但也并非没有质疑之声。法国地理学家边留久(Augustin Berque)就认为,当人们说风景源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时,实际上指的是关于风景的思考,这种思考需要借助语言,应当被称作“风景理论”(landscape theory);而“风景文化”(landscape thinking)并不一定需要语言,文艺复兴之前没有风景理论,但并不能说那时候的人不会欣赏风景,他们也有自己认识风景的方式,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景文化。在他看来,恰恰是风景理论排斥了风景文化(3-4)。不过,20 世纪下半叶之后,边留久所说的“风景理论”也在反思风景的词义嬗变引出的问题。一方面,“自然风光或风景画”作为“土地或地方”的再现,已经经过了意识形态的编码,隐含着权力关系;另一方面,风景的审美意义凸显,将“地方”客体化,影响了人们对人与栖息地关系的认识。 观看与权利
地理学者安特罗普(Marc Antrop)和埃特维尔德(Veerle Van Eetvelde)在《风景视角》(Landscape Perspectives)一书中总结了西方风景研究的历史。他们认为,西方的风景研究兴起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代,在19世纪之前主要是描绘、想象和设计风景,19世纪至20 世纪初有了地理学的参与,20 世纪以来更是呈现出跨学科的特征(12)。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的风景研究经历过两次重要的转向。米切尔认为,第一次转向与现代主义有关,主要是根据风景画的历史来理解风景的历史,如贡布里希的文章《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和风景画的兴起》;第二次则与后现代主义有关,转向了符号学和阐释学方法,把风景视为心理或意识形态主题的一种寓言(Introduction 1)。显然,第二次转向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学界日益重视语言、意义、再现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作用有关。
文化地理学家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认为,英语中将风景定义为从某一点看到的一片土地,这个观看地点使观者享有一种特权,可以选择、框定、组合自己的所见,用想象力将物质空间转换为风景(“Landscape” 254)。这种转换以观看(seeing)为媒介,而观看又必然受观看者的思想框架和文化背景制约。如迈尼格所说:“风景是由我们的视野来界定的,并由我们的头脑来解释”(Introduction 3);或如沙玛所言:“在感官接触风景之前,风景就已经在脑中了。景色是从一层层的记忆中构建出来的,这些记忆就像一层层的岩石一样”(6-7)。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总会有所选择,而且只能看到我们头脑或记忆中已有的东西。有鉴于此,科斯格罗夫借用伯格(John Berger)在1969 年提出的观点,不再把风景视为单纯的目光所见,而是一种包含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观看方式”(Social Formation 13;“ Landscape” 252)。
风景作为“观看方式”,涉及谁在看、在哪儿看、看到什么,而这些问题又关乎权力关系或意识形态问题。米切尔在《神圣的风景: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美国荒野》一文中指出:
主导了西方艺术史的风景概念,一直以视觉再现和图像再现为中心,即再现自然地表秀丽的、如画的、表面的样子。风景可以观看,但无法触及。它是地方的抽象化,空间的具体化。它被削减为从一定距离之外的视点看到的东西。这样一种远眺,借助一套相对可预见的传统——诗意的、如画的、崇高的、田园的等等——控制了风景,将风景框定起来,给风景编码。(265)也就是说,作为自然风光或风景画的风景,在经过文化的编码之后,将现实的“地方”转换成了再现的“空间”,从而掩盖或支持某种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抹杀或改写地方的历史,还会将这种行为隐藏起来或者使之合理化。如米切尔所言,描绘出来的风景“不仅仅是自然景色,也不仅仅是自然景色的再现,而是把这种对自然景色的再现变得如同天然而成”(“Imperial Landscape” 15)。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景不仅表征权力关系,而且是文化权力的工具(Introduction 1-2)。
达比(Wendy Joy Darby)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中提出,描绘某地的风景和“命名、制图、测量、居住”一样,都是一种权力施为,是“将空间殖民化”(50)。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帝国和阶级两个方面。奥威格认为,对“帝国风景”的描绘,可以通过有选择地呈现殖民地空间,否认或改写该地的文化和原住民(“Actual Landscape” 175)。例如,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19 世纪欧洲人写的非洲游记中发现,很多风景描写都“将当地居民与其所居之地分割开来”(126)。萨义德(Edward Said)也在《虚构、记忆和地方》一文中谈到,“一个地方的地理可以被改写、虚构和描绘,完全远离该地的实际情况”;“犹太复国主义就利用虚构的记忆,清空了巴勒斯坦的居民和历史,将该地的风景变为空无一物的空间”(246, 254)。早在其《东方学》(Orientalism)中,萨义德就探讨过虚构和建构出来的地理空间可以无视真实的地方,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和霸权关系(5)。
米切尔认为,帝国风景并不只是由本土向外扩张,也会反过来重新塑造本土。在他看来,英国近代的圈地运动,就是本土内部的殖民,使绿色的田野变成风景,从而成为民族和帝国身份的象征(“Imperial Landscape” 9, 17)。这种将本土地方变成风景的过程,掩盖了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英国18、19 世纪风景画中的青葱绿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想象和建构,用虚假的宁静祥和掩盖乡村劳动者的艰辛和乡村的阶级矛盾。艺术史学者伯明翰(Ann Birmingham)认为,英国18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如画”(picturesque)美学就是“试图抹去圈地运动的事实,并将其影响最小化”(75)。如画美学在赋予某个地方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抹去了劳动的痕迹。劳动者即便出现在视野中,也不过是点景人物。这实际上是用美学来掩盖政治、经济和道德问题。罗斯金(John Ruskin)在19 世纪中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现代画家》中说:“在小溪转弯处,我看到一个人在钓鱼,旁边有一个男孩和一只狗——这当然很如画,很悦目,如果他们没有一整天都在饿肚子的话”(269)。巴瑞尔(John Barrell)做了更为详尽的研究,他在《风景中的阴暗面:1730—1840 年间英国绘画中的乡村穷人》中考察了风景画中“穷人是如何被再现的(不如说是如何不被再现的)”,认为风景的再现不仅涉及审美,还涉及道德和社会问题(1)。
将地方再现为风景,在美学上是一种选择性的观看方式,在政治上则是一种排斥性的观看方式,同一片土地被分裂为“地方”和“景色”,也就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区分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对于在土地上劳动的农夫来说,土地就是生产空间;但对于欣赏自然风光的农业资产阶级来说,土地却主要是一种消费空间。这种空间的分裂不仅呼应了风景概念两层基本含义的分离,也体现着不同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18 世纪英国的土地所有者或农业资产阶级一方面靠作为生产空间的土地为生,剥削在土地上劳作的佃农;另一方面又通过建造宅邸和庭园,从视觉上排除谷仓、磨坊、农夫等“生产事实”,营造出一种没有农业劳动和农夫的“风景”,虚构了一个“未被破坏的”自然。农业资产阶级从自己乡宅的窗口、露台、草坪上俯视或远眺自己的土地,是一种审美的而非实用的观看方式,但这种观看又是以占有和控制土地为基础的(154-55)。即便观景者是游客而非这片土地的所有者,也不影响威廉斯观点的成立,因为在19 世纪中叶由铁路推动的大众旅游兴起之前,大部分游客都是从土地中获利的群体。如果说威廉斯区分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在18、19 世纪的英国主要涉及阶级问题,在20 世纪之后则更多涉及人的存在问题,也就是人与栖息地的关系问题。
观看与权利
地理学者安特罗普(Marc Antrop)和埃特维尔德(Veerle Van Eetvelde)在《风景视角》(Landscape Perspectives)一书中总结了西方风景研究的历史。他们认为,西方的风景研究兴起于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时代,在19世纪之前主要是描绘、想象和设计风景,19世纪至20 世纪初有了地理学的参与,20 世纪以来更是呈现出跨学科的特征(12)。值得注意的是,20 世纪的风景研究经历过两次重要的转向。米切尔认为,第一次转向与现代主义有关,主要是根据风景画的历史来理解风景的历史,如贡布里希的文章《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理论和风景画的兴起》;第二次则与后现代主义有关,转向了符号学和阐释学方法,把风景视为心理或意识形态主题的一种寓言(Introduction 1)。显然,第二次转向与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学界日益重视语言、意义、再现在建构社会现实中的作用有关。
文化地理学家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认为,英语中将风景定义为从某一点看到的一片土地,这个观看地点使观者享有一种特权,可以选择、框定、组合自己的所见,用想象力将物质空间转换为风景(“Landscape” 254)。这种转换以观看(seeing)为媒介,而观看又必然受观看者的思想框架和文化背景制约。如迈尼格所说:“风景是由我们的视野来界定的,并由我们的头脑来解释”(Introduction 3);或如沙玛所言:“在感官接触风景之前,风景就已经在脑中了。景色是从一层层的记忆中构建出来的,这些记忆就像一层层的岩石一样”(6-7)。也就是说,我们的目光总会有所选择,而且只能看到我们头脑或记忆中已有的东西。有鉴于此,科斯格罗夫借用伯格(John Berger)在1969 年提出的观点,不再把风景视为单纯的目光所见,而是一种包含了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的“观看方式”(Social Formation 13;“ Landscape” 252)。
风景作为“观看方式”,涉及谁在看、在哪儿看、看到什么,而这些问题又关乎权力关系或意识形态问题。米切尔在《神圣的风景:以色列、巴勒斯坦及美国荒野》一文中指出:
主导了西方艺术史的风景概念,一直以视觉再现和图像再现为中心,即再现自然地表秀丽的、如画的、表面的样子。风景可以观看,但无法触及。它是地方的抽象化,空间的具体化。它被削减为从一定距离之外的视点看到的东西。这样一种远眺,借助一套相对可预见的传统——诗意的、如画的、崇高的、田园的等等——控制了风景,将风景框定起来,给风景编码。(265)也就是说,作为自然风光或风景画的风景,在经过文化的编码之后,将现实的“地方”转换成了再现的“空间”,从而掩盖或支持某种权力。权力不仅可以抹杀或改写地方的历史,还会将这种行为隐藏起来或者使之合理化。如米切尔所言,描绘出来的风景“不仅仅是自然景色,也不仅仅是自然景色的再现,而是把这种对自然景色的再现变得如同天然而成”(“Imperial Landscape” 15)。从这个意义上说,风景不仅表征权力关系,而且是文化权力的工具(Introduction 1-2)。
达比(Wendy Joy Darby)在《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中提出,描绘某地的风景和“命名、制图、测量、居住”一样,都是一种权力施为,是“将空间殖民化”(50)。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帝国和阶级两个方面。奥威格认为,对“帝国风景”的描绘,可以通过有选择地呈现殖民地空间,否认或改写该地的文化和原住民(“Actual Landscape” 175)。例如,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在19 世纪欧洲人写的非洲游记中发现,很多风景描写都“将当地居民与其所居之地分割开来”(126)。萨义德(Edward Said)也在《虚构、记忆和地方》一文中谈到,“一个地方的地理可以被改写、虚构和描绘,完全远离该地的实际情况”;“犹太复国主义就利用虚构的记忆,清空了巴勒斯坦的居民和历史,将该地的风景变为空无一物的空间”(246, 254)。早在其《东方学》(Orientalism)中,萨义德就探讨过虚构和建构出来的地理空间可以无视真实的地方,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和霸权关系(5)。
米切尔认为,帝国风景并不只是由本土向外扩张,也会反过来重新塑造本土。在他看来,英国近代的圈地运动,就是本土内部的殖民,使绿色的田野变成风景,从而成为民族和帝国身份的象征(“Imperial Landscape” 9, 17)。这种将本土地方变成风景的过程,掩盖了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英国18、19 世纪风景画中的青葱绿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想象和建构,用虚假的宁静祥和掩盖乡村劳动者的艰辛和乡村的阶级矛盾。艺术史学者伯明翰(Ann Birmingham)认为,英国18 世纪后半叶兴起的“如画”(picturesque)美学就是“试图抹去圈地运动的事实,并将其影响最小化”(75)。如画美学在赋予某个地方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抹去了劳动的痕迹。劳动者即便出现在视野中,也不过是点景人物。这实际上是用美学来掩盖政治、经济和道德问题。罗斯金(John Ruskin)在19 世纪中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现代画家》中说:“在小溪转弯处,我看到一个人在钓鱼,旁边有一个男孩和一只狗——这当然很如画,很悦目,如果他们没有一整天都在饿肚子的话”(269)。巴瑞尔(John Barrell)做了更为详尽的研究,他在《风景中的阴暗面:1730—1840 年间英国绘画中的乡村穷人》中考察了风景画中“穷人是如何被再现的(不如说是如何不被再现的)”,认为风景的再现不仅涉及审美,还涉及道德和社会问题(1)。
将地方再现为风景,在美学上是一种选择性的观看方式,在政治上则是一种排斥性的观看方式,同一片土地被分裂为“地方”和“景色”,也就是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区分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对于在土地上劳动的农夫来说,土地就是生产空间;但对于欣赏自然风光的农业资产阶级来说,土地却主要是一种消费空间。这种空间的分裂不仅呼应了风景概念两层基本含义的分离,也体现着不同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指出,18 世纪英国的土地所有者或农业资产阶级一方面靠作为生产空间的土地为生,剥削在土地上劳作的佃农;另一方面又通过建造宅邸和庭园,从视觉上排除谷仓、磨坊、农夫等“生产事实”,营造出一种没有农业劳动和农夫的“风景”,虚构了一个“未被破坏的”自然。农业资产阶级从自己乡宅的窗口、露台、草坪上俯视或远眺自己的土地,是一种审美的而非实用的观看方式,但这种观看又是以占有和控制土地为基础的(154-55)。即便观景者是游客而非这片土地的所有者,也不影响威廉斯观点的成立,因为在19 世纪中叶由铁路推动的大众旅游兴起之前,大部分游客都是从土地中获利的群体。如果说威廉斯区分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在18、19 世纪的英国主要涉及阶级问题,在20 世纪之后则更多涉及人的存在问题,也就是人与栖息地的关系问题。 4. 人与栖息地
如果风景仅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就印证了威廉斯的那句名言:“风景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分离与观看”(265);观看风景的人,始终是从一定的距离之外欣赏风景。科斯格罗夫把观景的人称作“外部人”(outsider),而以土地为生计和家园的人无法与土地分离,属于“内部人”(insider),土地对他们而言主要是地方而不是景色(Social Formation 19)。对于同一片土地,“外部人”看到了景色,却不属于这个地方,这里对他来说是消费空间;而“内部人”虽然属于这个地方,却又看不到景色,这里对他来说只是生产空间。这也就意味着当风景仅指自然风光而非地方时,人就无法“属于”风景。这种由概念引起的悖论显然影响了人们对人与栖息地关系的认识。随着20 世纪70 年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有学者主张将风景概念的两层基本含义“地方”和“景色”,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侧重分离和观看转向强调关联和体验。
马尔帕斯(Jeff Malpas)在《地方与风景问题》一文中反对将风景分为“生活的”(lived)和“再现的”(represented)两个层面,因为在再现地方之前,人们就已经与地方发生了关系:“只有在我们与地方产生了关系之后,风景才会出现。那个地方通过它的声音、气味、情感和景色影响了我们,而且可以说,是通过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行动影响了我们,我们也因此在那个地方发现了自己”(11, 13) 。在他看来,“风景无论是作为生活的地方,还是作为再现的作品,总涉及积极的参与和体验”(19),而自我也正是在这种参与和体验中形成的:“风景可能是在人的干预下形成的,但人自身一定是风景塑造的。在这种关系中,没有哪一方占据上风——双方都在影响并适应对方”(17)。当我们不再把风景分裂为地方和景色的时候,风景也就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成了我们赖以形成的东西。人与风景的关系也就不再是分离,而是关联。
哈佛大学摄影学教授凯尔西(Robin Kelsey)发现,当代的风景研究格外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但他认为现在有必要“从强调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转向强调物种与栖息地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204)。他在《侧身风景之外》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采取的是一种凌驾于风景之上的态度,认为风景属于我们,但我们不属于风景。这其实是“一种幻想,幻想自己不属于一片土地上的总体生活”(204)。其根源就在于把“地方”与“景色”分离开了,也就是马尔帕斯所说的将风景分为“生活的”和“再现的”,或威廉斯所说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凯尔西承认,现代人在审美上渴望能够融入风景。例如,有浪漫情怀的人渴望能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有怀旧情愫的人认为我们曾经是风景的一部分,并渴望能够再度回到风景之中。但问题在于,这两种渴望的前提都是认为自己并不属于风景(208)。从生态的角度看,“不属于风景”实际上只是人们的幻想,但要打破这种幻想,重新回到风景之中,又意味着限制和责任,意味着要使人类与其他物种平起平坐。凯尔西认为,这种生态视角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行合一。他举例说,人们现在或许不难认识到自己的一些消费方式,如乘坐飞机和使用空调,可能会影响全球气候,但是否愿意因此而放弃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舒适和便捷,就不一定了(210)。这也是一个亟待我们思考和应对的问题,因为保护环境实质上是保护人类自身。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真正面临危险的不是地球,而是人类的未来,人们现在需要走出我们能够保护自然的“迷思”(156)。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风景是什么的认识,也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风景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要寻求二者的关联和交融,不仅需要弥合风景的两层基本含义之间的鸿沟,还要进一步整合风景研究的不同路径。这一点也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风景的研究历史来看,风景的两层含义带来了看待风景的两大角度,即段义孚所说的“功能性的”和“道德—审美的”角度(89-90);后者将风景视为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关注风景是如何被感知、阐释和再现的。怀特(Ian D. Whyte)在《16 世纪以来的风景与历史》中认为,这是一种主观的研究方法,代表人物有阿普尔顿(Jay Appleton)、科斯格罗夫、米切尔、伯格等。怀特认为西方的风景研究还有一种客观的方法,关注自然与人类力量在一段时间内对风景的改变,代表人物有历史学家霍斯金斯(W. G. Hoskins)、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等(15-26)。这两种方法在20 世纪的风景研究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特罗普和埃特维尔德认为,现在有必要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因为风景“从各种比例和各种层面,融合了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美学、地理与历史、人类与环境。风景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的地方,是空间与时间交汇的地方”(4)。面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建构一种整体的(holistic)风景观显得尤为迫切。这种风景观不再区分“地方”与“景色”,而是将二者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改变我们对人与栖息地关系的认识,进而改变我们的存在状态。
4. 人与栖息地
如果风景仅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就印证了威廉斯的那句名言:“风景概念本身就意味着分离与观看”(265);观看风景的人,始终是从一定的距离之外欣赏风景。科斯格罗夫把观景的人称作“外部人”(outsider),而以土地为生计和家园的人无法与土地分离,属于“内部人”(insider),土地对他们而言主要是地方而不是景色(Social Formation 19)。对于同一片土地,“外部人”看到了景色,却不属于这个地方,这里对他来说是消费空间;而“内部人”虽然属于这个地方,却又看不到景色,这里对他来说只是生产空间。这也就意味着当风景仅指自然风光而非地方时,人就无法“属于”风景。这种由概念引起的悖论显然影响了人们对人与栖息地关系的认识。随着20 世纪70 年代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有学者主张将风景概念的两层基本含义“地方”和“景色”,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侧重分离和观看转向强调关联和体验。
马尔帕斯(Jeff Malpas)在《地方与风景问题》一文中反对将风景分为“生活的”(lived)和“再现的”(represented)两个层面,因为在再现地方之前,人们就已经与地方发生了关系:“只有在我们与地方产生了关系之后,风景才会出现。那个地方通过它的声音、气味、情感和景色影响了我们,而且可以说,是通过我们自己和他人的行动影响了我们,我们也因此在那个地方发现了自己”(11, 13) 。在他看来,“风景无论是作为生活的地方,还是作为再现的作品,总涉及积极的参与和体验”(19),而自我也正是在这种参与和体验中形成的:“风景可能是在人的干预下形成的,但人自身一定是风景塑造的。在这种关系中,没有哪一方占据上风——双方都在影响并适应对方”(17)。当我们不再把风景分裂为地方和景色的时候,风景也就不再是身外之物,而成了我们赖以形成的东西。人与风景的关系也就不再是分离,而是关联。
哈佛大学摄影学教授凯尔西(Robin Kelsey)发现,当代的风景研究格外关注意识形态问题,但他认为现在有必要“从强调阶级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转向强调物种与栖息地之间的意识形态距离”,以应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204)。他在《侧身风景之外》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采取的是一种凌驾于风景之上的态度,认为风景属于我们,但我们不属于风景。这其实是“一种幻想,幻想自己不属于一片土地上的总体生活”(204)。其根源就在于把“地方”与“景色”分离开了,也就是马尔帕斯所说的将风景分为“生活的”和“再现的”,或威廉斯所说的生产空间和消费空间。凯尔西承认,现代人在审美上渴望能够融入风景。例如,有浪漫情怀的人渴望能够成为风景的一部分,有怀旧情愫的人认为我们曾经是风景的一部分,并渴望能够再度回到风景之中。但问题在于,这两种渴望的前提都是认为自己并不属于风景(208)。从生态的角度看,“不属于风景”实际上只是人们的幻想,但要打破这种幻想,重新回到风景之中,又意味着限制和责任,意味着要使人类与其他物种平起平坐。凯尔西认为,这种生态视角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行合一。他举例说,人们现在或许不难认识到自己的一些消费方式,如乘坐飞机和使用空调,可能会影响全球气候,但是否愿意因此而放弃这种消费方式带来的舒适和便捷,就不一定了(210)。这也是一个亟待我们思考和应对的问题,因为保护环境实质上是保护人类自身。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言,真正面临危险的不是地球,而是人类的未来,人们现在需要走出我们能够保护自然的“迷思”(156)。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风景是什么的认识,也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
风景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非人世界的交流。要寻求二者的关联和交融,不仅需要弥合风景的两层基本含义之间的鸿沟,还要进一步整合风景研究的不同路径。这一点也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从风景的研究历史来看,风景的两层含义带来了看待风景的两大角度,即段义孚所说的“功能性的”和“道德—审美的”角度(89-90);后者将风景视为社会和文化的产物,关注风景是如何被感知、阐释和再现的。怀特(Ian D. Whyte)在《16 世纪以来的风景与历史》中认为,这是一种主观的研究方法,代表人物有阿普尔顿(Jay Appleton)、科斯格罗夫、米切尔、伯格等。怀特认为西方的风景研究还有一种客观的方法,关注自然与人类力量在一段时间内对风景的改变,代表人物有历史学家霍斯金斯(W. G. Hoskins)、地理学家索尔(Carl Sauer)等(15-26)。这两种方法在20 世纪的风景研究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安特罗普和埃特维尔德认为,现在有必要将这两种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因为风景“从各种比例和各种层面,融合了自然与文化、科学与美学、地理与历史、人类与环境。风景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合的地方,是空间与时间交汇的地方”(4)。面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建构一种整体的(holistic)风景观显得尤为迫切。这种风景观不再区分“地方”与“景色”,而是将二者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以改变我们对人与栖息地关系的认识,进而改变我们的存在状态。 从风景到山水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风景概念主要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实际上是将风景视为客体,而作为主体的我们则侧身风景之外。如沃勒克(Alan Wallach)所言,西方风景传统的核心就是一种建立在“我—它”、自我与他者、观者与被观者基础上的主体—客体关系(317)。这种强调分离与观看的风景传统显然不利于人与栖息地的交融。近年来,以法国汉学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和地理学家边留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尝试借鉴中国的山水思想,消除西方风景概念中隐含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把风景视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或资源。
朱利安在《山水之间,或理性的未思》(Living Off Landscape or the Unthought-of in Reason)中提出,“风景”是典型的欧洲词语,如弗莱芒语中的landschap、德语中的Landschaft、英语中的landscape、法语中的paysage、意大利语中的paesaggio、西班牙语中的paisaje、俄语中的пейзаж(2)。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词汇,如“山水”和“风景”。“山水”原指山和水两种地理形态,或山中之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渐渐开始指由丘石林泉构成的优美环境,由地理词汇变成了美学词汇。中文中的“风景”一词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指风光景致。相对而言,“山水”使用的频率更高,也一直是中国风景的主体(吴静子、王其亨 29-47;刘洁 11-12)。不过,无论是中文中的“风景”还是“山水”,都不像西方的风景概念那样凸显观者与景色、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宗白华在分析中西风景画法的不同境界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123)。
朱利安认为欧洲的风景概念存在三大偏见:一是忽视整体,将风景当作观者的目光从大地上剪裁出的“一部分”;二是过于强调视觉,将观看当作进入风景的唯一方式;三是主体与客体分离,将观者与大自然对立起来(Living Off 5)。第一个偏见使风景拘囿于目光所及之处,并将目光所框定的这部分土地抽象为一个均质的几何空间,抹杀了土地的个性;第二个偏见把风景减缩为表象,并使观者脱离了听觉和味觉等感觉所依赖的环境氛围;第三个偏见不仅使人与世界对立起来,还使人与世界分离开来(7-9)。
显然,这三个偏见都与观看有关,朱利安对欧洲风景概念的修正也是由此入手。他认为第一应该区分“风景”(landscape)和“所见之景”(view)。“所见之景”是将视线投向客体,有一个固定的焦点;而“风景”需要使目光移动起来,不受固定焦点的束缚。第二应该区分“用眼睛看”(with my eyes)和“通过眼睛去看”(through my eyes):对前者而言,眼睛是使动者,是主体在观察事物,通过视线来描述客体;而对于后者,眼睛只是中介,主体不是在看“什么”,而是在看,目光不再固定,而是游移于事物之间,风景也由是进入了观者的内心——观察(observe)变成了静观(contemplate; 10-14)。
朱利安发现中国的山水观有助于纠正欧洲风景概念的上述偏颇。欧洲人将风景视为视线从大地上剪裁出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山水则强调“山”和“水”这组对立事物的关联。山水包含了高低、纵横、静动、常变、虚实、有形与无形、不透明与透明。山与水的两极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的存在有赖于另一方。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呈现在眼前的大自然,因为大自然乃是两极之间的互动;也没有了独立于风景之外的观者,因为观者就在山与水之间,在山水之内(Living Off 15-16)。
朱利安还发现,中国的山水画与西方的风景画也反映了上述不同。北宋画家郭熙在其画论《山水训》中提出了山有“三远”之说:“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51)。朱利安认为,高远、深远、平远分别对应着仰、窥、望三种观看方式,强调视线的移动,可以组织出多重视角,不像西方风景画那样固定在一个观察点、集中在一个焦点观看(Living Off 34-35)。郭熙还提出,“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40)。朱利安认为,虽然可行和可望涉及客体和距离,但可居强调风景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人类生活的环境。因此,山水的价值不在于审美(强调分离、客体、观看),而在于滋养生命(强调身处其中、交融、生活;Living Off 36-40)。如此一来,风景便“不再只是被‘观看’或‘再现’,而是与生命联系在了一起”;“不再像通常所定义的那样,是大自然‘呈现’给‘观者’的大地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生活可以无限汲取的资源”(x)。
朱利安还在《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一书中解释了中国的山水思想何以能打破西方风景概念的主客体之分。一方面,他援引苏东坡的名句“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来说明山水“大象无形”(山水画也因此追求传神而不求形似),乃是两极之间的互动和无穷交会,包含了一切使万物富有生机的东西,因而无法被客体化(278-79, 259-61);另一方面,他又援引石涛的名句“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来说明人与山水同源,都是“气”的产物,山水与人乃是伙伴关系,也就无所谓主客体之分(279-82)。关于第二个方面,朱利安还借用南朝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山水“质有而趣灵”一说,认为山水兼具物质(质有)与精神(趣灵)特性。这两种特性之间并没有裂隙,因为山水散发着气韵(aura),而气韵既不属于形体也不属于神灵,既不属于可见也不属于不可见,而是将二者笼罩在了一起(Living Off 59, 63)。边留久也意识到宗炳所说的“质有而趣灵”已经指出了山水的两面性:一面是“物质的、可见的事物”,一面是“非物质的、不可见的关系”(45)。在他看来,西方将风景视为客体,也就抹杀了“趣灵”,“导致了风景的消亡”(51)。因此,他认为“发明风景”这个说法并不恰当,是在强调风景只是人类目光凝视的产物;应该说“风景的诞生”,因为“风景并非存在于对客体的凝视之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之中,换言之,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与环境的关系之中”(30)。
从风景到山水
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风景概念主要指自然风光或风景画,实际上是将风景视为客体,而作为主体的我们则侧身风景之外。如沃勒克(Alan Wallach)所言,西方风景传统的核心就是一种建立在“我—它”、自我与他者、观者与被观者基础上的主体—客体关系(317)。这种强调分离与观看的风景传统显然不利于人与栖息地的交融。近年来,以法国汉学家朱利安(François Jullien)和地理学家边留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尝试借鉴中国的山水思想,消除西方风景概念中隐含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距离,把风景视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或资源。
朱利安在《山水之间,或理性的未思》(Living Off Landscape or the Unthought-of in Reason)中提出,“风景”是典型的欧洲词语,如弗莱芒语中的landschap、德语中的Landschaft、英语中的landscape、法语中的paysage、意大利语中的paesaggio、西班牙语中的paisaje、俄语中的пейзаж(2)。其实,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词汇,如“山水”和“风景”。“山水”原指山和水两种地理形态,或山中之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渐渐开始指由丘石林泉构成的优美环境,由地理词汇变成了美学词汇。中文中的“风景”一词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指风光景致。相对而言,“山水”使用的频率更高,也一直是中国风景的主体(吴静子、王其亨 29-47;刘洁 11-12)。不过,无论是中文中的“风景”还是“山水”,都不像西方的风景概念那样凸显观者与景色、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宗白华在分析中西风景画法的不同境界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为物我对立的,一为物我浑融的”(123)。
朱利安认为欧洲的风景概念存在三大偏见:一是忽视整体,将风景当作观者的目光从大地上剪裁出的“一部分”;二是过于强调视觉,将观看当作进入风景的唯一方式;三是主体与客体分离,将观者与大自然对立起来(Living Off 5)。第一个偏见使风景拘囿于目光所及之处,并将目光所框定的这部分土地抽象为一个均质的几何空间,抹杀了土地的个性;第二个偏见把风景减缩为表象,并使观者脱离了听觉和味觉等感觉所依赖的环境氛围;第三个偏见不仅使人与世界对立起来,还使人与世界分离开来(7-9)。
显然,这三个偏见都与观看有关,朱利安对欧洲风景概念的修正也是由此入手。他认为第一应该区分“风景”(landscape)和“所见之景”(view)。“所见之景”是将视线投向客体,有一个固定的焦点;而“风景”需要使目光移动起来,不受固定焦点的束缚。第二应该区分“用眼睛看”(with my eyes)和“通过眼睛去看”(through my eyes):对前者而言,眼睛是使动者,是主体在观察事物,通过视线来描述客体;而对于后者,眼睛只是中介,主体不是在看“什么”,而是在看,目光不再固定,而是游移于事物之间,风景也由是进入了观者的内心——观察(observe)变成了静观(contemplate; 10-14)。
朱利安发现中国的山水观有助于纠正欧洲风景概念的上述偏颇。欧洲人将风景视为视线从大地上剪裁出的一部分,而中国的山水则强调“山”和“水”这组对立事物的关联。山水包含了高低、纵横、静动、常变、虚实、有形与无形、不透明与透明。山与水的两极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方的存在有赖于另一方。这样一来,也就不存在呈现在眼前的大自然,因为大自然乃是两极之间的互动;也没有了独立于风景之外的观者,因为观者就在山与水之间,在山水之内(Living Off 15-16)。
朱利安还发现,中国的山水画与西方的风景画也反映了上述不同。北宋画家郭熙在其画论《山水训》中提出了山有“三远”之说:“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51)。朱利安认为,高远、深远、平远分别对应着仰、窥、望三种观看方式,强调视线的移动,可以组织出多重视角,不像西方风景画那样固定在一个观察点、集中在一个焦点观看(Living Off 34-35)。郭熙还提出,“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40)。朱利安认为,虽然可行和可望涉及客体和距离,但可居强调风景不只是用来看的,更是人类生活的环境。因此,山水的价值不在于审美(强调分离、客体、观看),而在于滋养生命(强调身处其中、交融、生活;Living Off 36-40)。如此一来,风景便“不再只是被‘观看’或‘再现’,而是与生命联系在了一起”;“不再像通常所定义的那样,是大自然‘呈现’给‘观者’的大地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生活可以无限汲取的资源”(x)。
朱利安还在《大象无形:或论绘画之非客体》一书中解释了中国的山水思想何以能打破西方风景概念的主客体之分。一方面,他援引苏东坡的名句“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来说明山水“大象无形”(山水画也因此追求传神而不求形似),乃是两极之间的互动和无穷交会,包含了一切使万物富有生机的东西,因而无法被客体化(278-79, 259-61);另一方面,他又援引石涛的名句“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来说明人与山水同源,都是“气”的产物,山水与人乃是伙伴关系,也就无所谓主客体之分(279-82)。关于第二个方面,朱利安还借用南朝画家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的山水“质有而趣灵”一说,认为山水兼具物质(质有)与精神(趣灵)特性。这两种特性之间并没有裂隙,因为山水散发着气韵(aura),而气韵既不属于形体也不属于神灵,既不属于可见也不属于不可见,而是将二者笼罩在了一起(Living Off 59, 63)。边留久也意识到宗炳所说的“质有而趣灵”已经指出了山水的两面性:一面是“物质的、可见的事物”,一面是“非物质的、不可见的关系”(45)。在他看来,西方将风景视为客体,也就抹杀了“趣灵”,“导致了风景的消亡”(51)。因此,他认为“发明风景”这个说法并不恰当,是在强调风景只是人类目光凝视的产物;应该说“风景的诞生”,因为“风景并非存在于对客体的凝视之中,而是存在于现实之中,换言之,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与环境的关系之中”(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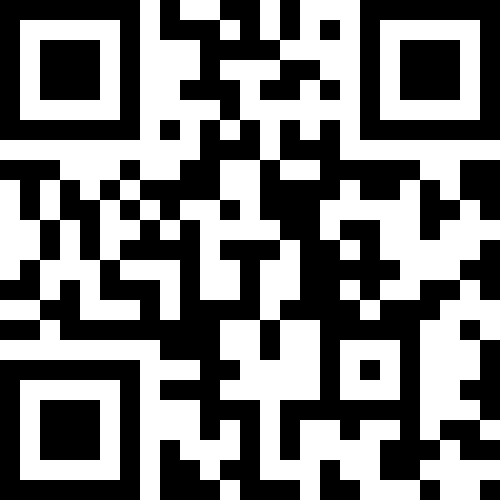 本文发表于《外国文学》2023年第4期,更多文章信息
请扫描上方二维码或复制链接(https://sourl.cn/mAYGN2)到浏览器,移步知网下载
期
刊
在线阅读及其下载
在学术期刊官网,阅读全文
https://www.bfsujournals.com/c/2019-07-18/486526.shtml
在知网下载期刊全文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tYqgYjzYKsDSiPqMb_JlxDh5l_G-6d0jvyMO5rJ0Jy2VngJdW87prC6pL7TTDlx_75CfRWNj8tHTfLC5tvzHi_fEAaxme6iwD5SOmK6Kh5Qeveorb01GLA==&uniplatform=NZKPT
本文发表于《外国文学》2023年第4期,更多文章信息
请扫描上方二维码或复制链接(https://sourl.cn/mAYGN2)到浏览器,移步知网下载
期
刊
在线阅读及其下载
在学术期刊官网,阅读全文
https://www.bfsujournals.com/c/2019-07-18/486526.shtml
在知网下载期刊全文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tYqgYjzYKsDSiPqMb_JlxDh5l_G-6d0jvyMO5rJ0Jy2VngJdW87prC6pL7TTDlx_75CfRWNj8tHTfLC5tvzHi_fEAaxme6iwD5SOmK6Kh5Qeveorb01GLA==&uniplatform=NZKP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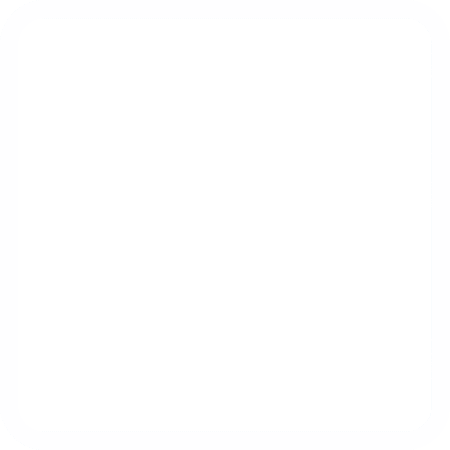 期刊介绍
本刊创办于1980年,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刊物之一,主要栏目包括评论、理论、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书评等。
荣誉及数据库收录: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数据库收录,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22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和“2018最受学界欢迎的20种学术期刊(人文学科类)”。
期刊介绍
本刊创办于1980年,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刊物之一,主要栏目包括评论、理论、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研究、书评等。
荣誉及数据库收录: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CNKI数据库收录,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来源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2022年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核心期刊和“2018最受学界欢迎的20种学术期刊(人文学科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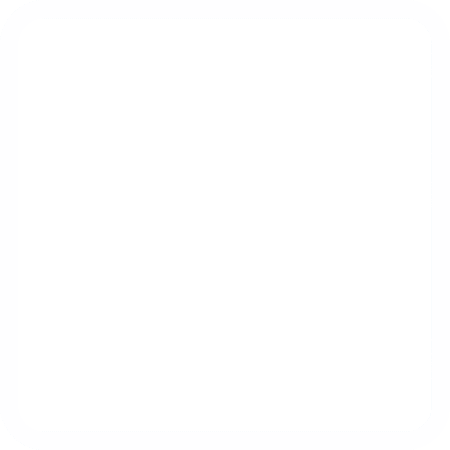 期刊订阅方式
中国邮政订阅:
邮发代码:2-450
国内统一刊号:CN11-1248/I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5529
1、各地邮局期刊征订处
2、订阅拨打中国邮政官方电话11185订阅
淘宝、天猫电商销售:
单期购买。通过外研社天猫旗舰店购买当期以及过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id=731796377346&rn=cf22f10704b9d5b494022dc143078467&spm=a1z10.3-b-s.w4011-22665586135.102.779137e9NOmEly&skuId=5070249833617
往期精选
外国文学 | 论中世纪英国的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文/李维屏)
外国文学 | 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悖论(文/赵 淳)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5期目录及摘要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4期目录及摘要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3期目录及摘要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外国文学| 西方文论关键词:新物质主义(文/韩启群)
刊讯 | 《外国文学》(2023年第1期)目录及其摘要
外国文学| 西方文论关键词:非个人化(文/许小凡)
刊讯| 《外国文学》2022年第六期目录及其摘要
重磅通知︱必看的11本优秀学术期刊
外国文学 | 诗人、超灵与“解救万物的诸神” ——爱默生论莎士比亚及其内在悖论
期刊概览:《外国文学》(2022年第5期)目录及其摘要
《外国文学》编辑部召开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与阐释”工作推进会
外国文学 | 西方文论关键词:接受美学(文/任卫东)
祝贺《外国文学》进入文学类学术期刊Q1区!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
转载请注明来自微信订阅号:北外学术期刊
北外学术期刊官网:https://www.bfsujournals.com/
欢迎分享与转发
期刊订阅方式
中国邮政订阅:
邮发代码:2-450
国内统一刊号:CN11-1248/I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5529
1、各地邮局期刊征订处
2、订阅拨打中国邮政官方电话11185订阅
淘宝、天猫电商销售:
单期购买。通过外研社天猫旗舰店购买当期以及过刊。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1&id=731796377346&rn=cf22f10704b9d5b494022dc143078467&spm=a1z10.3-b-s.w4011-22665586135.102.779137e9NOmEly&skuId=5070249833617
往期精选
外国文学 | 论中世纪英国的共同体思想与文学想象(文/李维屏)
外国文学 | 拉康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悖论(文/赵 淳)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5期目录及摘要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4期目录及摘要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3期目录及摘要
刊讯|《外国文学》2023年第2期目录及摘要
外国文学| 西方文论关键词:新物质主义(文/韩启群)
刊讯 | 《外国文学》(2023年第1期)目录及其摘要
外国文学| 西方文论关键词:非个人化(文/许小凡)
刊讯| 《外国文学》2022年第六期目录及其摘要
重磅通知︱必看的11本优秀学术期刊
外国文学 | 诗人、超灵与“解救万物的诸神” ——爱默生论莎士比亚及其内在悖论
期刊概览:《外国文学》(2022年第5期)目录及其摘要
《外国文学》编辑部召开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与阐释”工作推进会
外国文学 | 西方文论关键词:接受美学(文/任卫东)
祝贺《外国文学》进入文学类学术期刊Q1区!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原文
转载请注明来自微信订阅号:北外学术期刊
北外学术期刊官网:https://www.bfsujournals.com/
欢迎分享与转发




